老汉下地锄草,坐下休息时,一只黄鼠狼跳到他锄头上跳起了舞,手中还折断了两朵野花,把老汉给看乐了,老汉笑着说:“你还真像个跳舞的人娃娃”。 这场景要是搁在别人眼里,或许就是山野间一段趣闻,可对鲁中乡下的王老汉来说,这只立起身、晃着野花的黄鼠狼,像是一道劈开生活迷雾的光。 王老汉那年六十出头,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得厉害。 家里有个三十岁的儿子,生下来就痴痴呆呆,连句完整的“爹”都喊不清。 老两口守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像田埂上的草,风吹雨打,就盼着能有个挺直腰杆的盼头。 那天午后日头正毒,老汉歇在地头抽烟,黄鼠狼突然从草棵里窜出来,后腿立着,前爪举着两朵黄灿灿的野花,在锄头上一扭一扭,那模样,真跟戏台上画着花脸的小娃娃似的。 老汉当时没多想,只当是山里精怪讨食吃,从布袋里摸出个没吃完的窝头,掰了块放在地上。 黄鼠狼却没吃,只是用鼻子嗅了嗅,又对着老汉作了个揖,尾巴一甩就钻进了玉米地。 等老汉傍晚扛着锄头回家,发现门槛上放着颗圆滚滚、黄澄澄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沉甸甸的,在油灯下泛着柔光,是颗金豆子。 本来想把金豆子换了给儿子瞧病,可夜里老两口合计了半宿,总觉得这东西来得蹊跷。 老伴抹着眼泪说:“这怕是仙家显灵,咱不能白受这份情。” 第二天一早,老两口揣着金豆子去了镇上,没找郎中,反倒寻了个木匠,商量着在村后破庙的地基上,盖间小祠堂。 祠堂不大,就一间屋,泥墙草顶,里头供着个用桃木刻的小像,模样照着那天跳舞的黄鼠狼,手里也捏着两朵野花。 打那以后,老伴每天都带着儿子去祠堂上香。 儿子虽然痴傻,却记得每天给香炉添把新米,有时还对着木像嘿嘿笑。 老汉依旧下地干活,只是路过祠堂时,总忍不住往里头望一眼,看着袅袅的青烟,心里那点苦似乎也淡了些。 这样过了大半年,村里有人说老汉老糊涂了,供着个畜生当神仙;也有人说,祠堂盖起来后,山里的野兔都少了,庄家收成反倒好了些。 变故发生在开春后的一个集日。 老汉去镇上卖粮食,在牲口市旁边看见个猎户摆摊,摊上挂着张黄澄澄的皮子,毛茸茸的尾巴拖在地上,是张完整的黄鼠狼皮。 猎户叼着烟说:“前儿个在后山打着的,这畜生邪门得很,中了箭还立起来想扑人,跟个人似的。” 老汉心里“咯噔”一下,想起祠堂里的木像,没敢多问,掏光了身上卖粮食的钱,把那张皮买了回来。 回到家,老伴见了皮子就哭了,说这准是得罪了仙家。 老两口连夜把皮子拿到祠堂,小心翼翼地披在桃木像上。 那天夜里,祠堂的油灯亮了一宿。 转天早上,老汉去祠堂添水,发现桃木像上的皮子不见了,地上只留着一小撮黄毛,而里屋传来儿子的声音,虽然含糊,却清清楚楚:“爹……饿……” 如今祠堂还在村后,泥墙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斑驳,里头的桃木像依旧捏着野花。 王老汉的儿子后来渐渐好了,能帮着家里挑水劈柴,虽然话不多,但见了人会笑,会喊“叔”“婶”。 有人问老汉,那黄鼠狼到底是不是仙家,老汉总是摆摆手,说:“就是只通人性的畜生。” 只是每当傍晚,他坐在地头抽烟,看见风吹过玉米叶沙沙响,总会想起那天午后,锄头上那个晃着野花的小身影,心里觉得,日子再难,只要有那么点念想,就总能熬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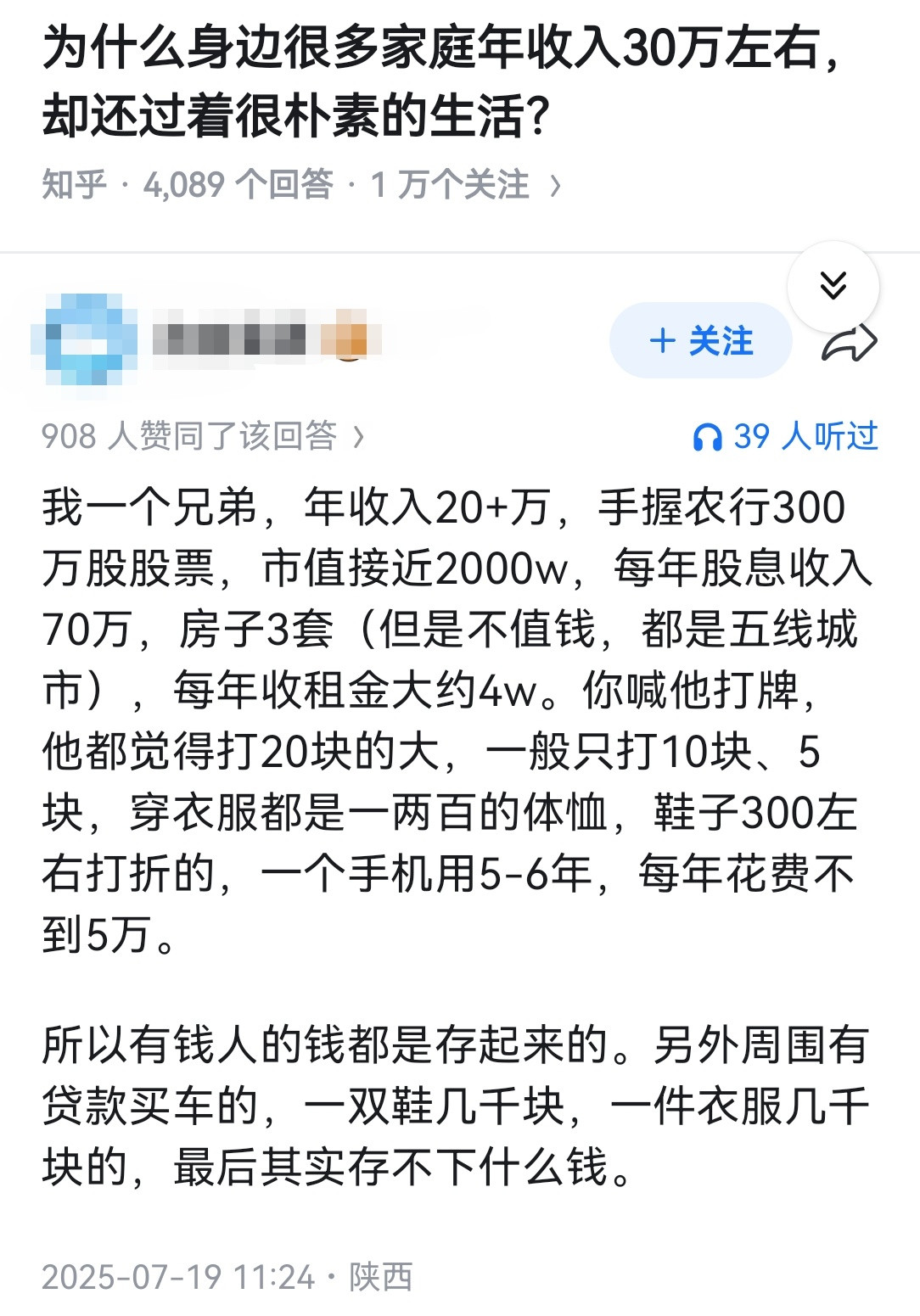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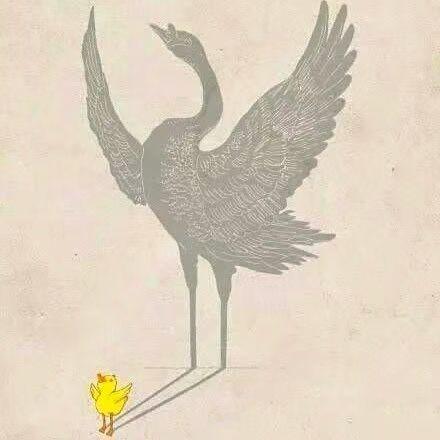






我叫大林子
主业上班班,副业炒个股。逻辑是行事的唯一准则。阔以聊一下数学和逻辑,其它就算了吧。比如地支申亥,遇蛇年,那些疾病和交通事故我一个都没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