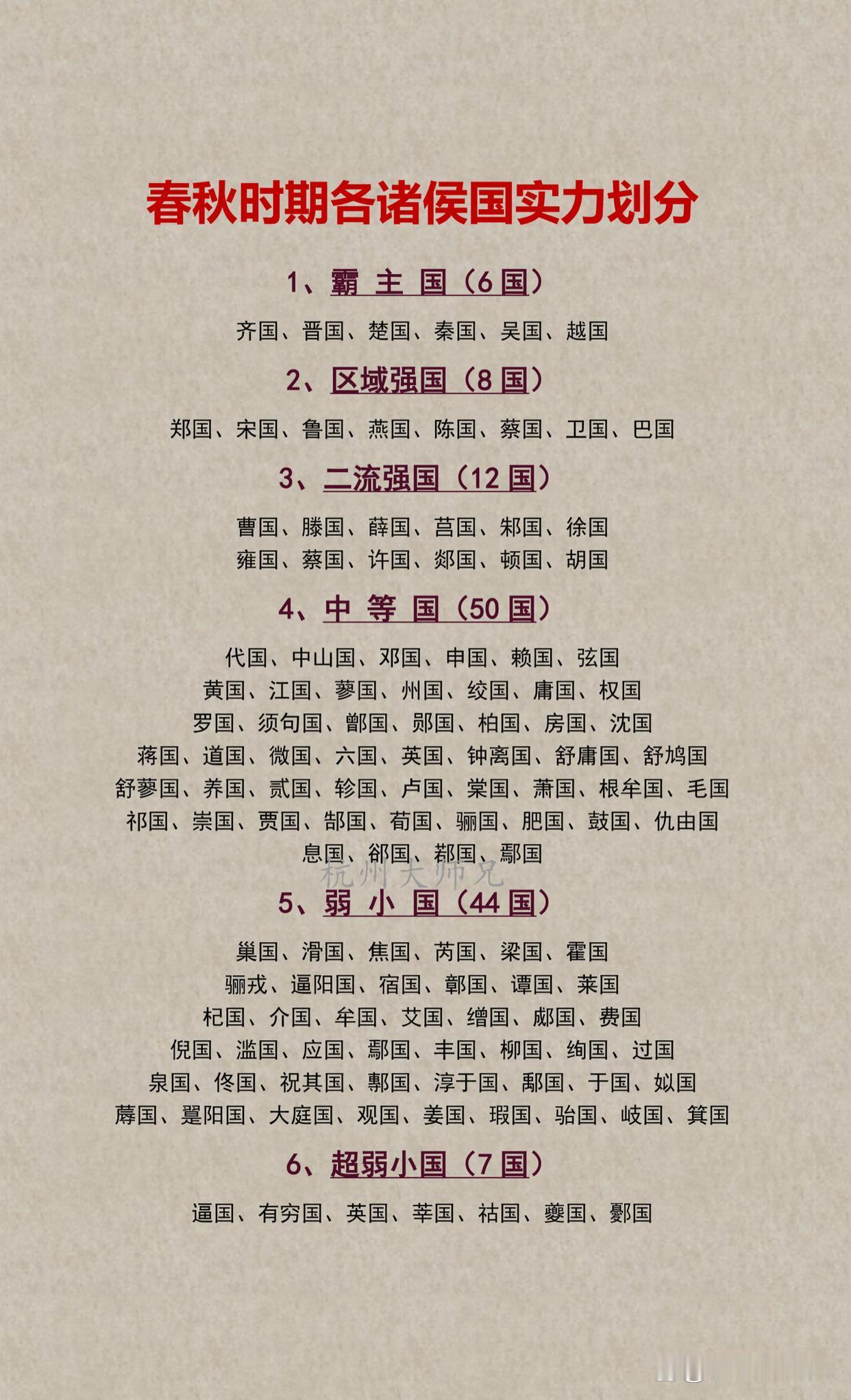王昭君21岁时,丈夫刚去世,继子就冲进帐篷一把搂住她。王昭君瑟瑟发抖,气得打了他一巴掌,怒道:“你疯了!”可是没多久,王昭君就嫁给了继子,还为他生了2个女儿。 帐篷里那股羊膻味混着马奶酒的气息还没散尽,王昭君缩在毡毯上,手指还在发颤。那一巴掌打得她掌心发麻,可更让她心慌的是复株累那双眼睛,不像草原狼盯着猎物,倒像迷路的人突然看见灯火。帐外风声呜咽,她想起长安的秋夜,桂花的甜香能飘进未央宫的檐角,而这里,只有无尽草浪和刮得人脸生疼的风。 老单于呼韩邪的葬礼持续了三天三夜。篝火烧红半边天,萨满的鼓声敲得人心头发慌。王昭君看着那些披黑毡的匈奴贵族,忽然明白一件事:在这片草原上,汉家公主的封号轻得像绒毛,真正重的是你属于哪个帐篷,是谁的妻子。侍女悄悄告诉她,按照匈奴祖制,父亲去世,长子可以继承除了生母之外的所有女眷。话没说完,王昭君手里的铜镜“哐当”掉在地上。 她想起出塞那年刚满十九,车辇过了雁门关,回头再也望不见汉家城墙。送亲的使节念着皇上恩典,说公主此去是为两国永好。那时她抱紧怀里的琵琶,心想这辈子大概就像这把琴,拨什么音不由自己。可当真见到呼韩邪,那个鬓角已斑白、笑起来眼角皱纹很深的匈奴王,他下马亲自扶她下车,用生硬的汉语说:“长安来的鸿雁,草原不会亏待你。”两年光景,他教她骑马,允许她在帐后种一小片从中原带来的菊,夜里听她弹《阳关三叠》从不打断。那或许不是少女憧憬的情爱,却是乱世里难得的安稳。 现在这安稳碎了。复株累成为新单于的第七天,王昭君帐前的守卫换了一批人。老侍女抹着泪收拾箱笼,把汉式曲裾深衣一件件叠好,低声说:“公主,咱们得往东帐搬了。”王昭君盯着案上那封还没写完寄往长安的家书,墨迹被眼泪晕开一团灰影。她忽然抓起信纸扔进火盆,看火舌窜起来舔尽所有“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之类的字句——长安太远了,远到没人能告诉她此刻该不该再死一次。 嫁复株累那晚没有红绸。她穿着匈奴阏氏的礼服,沉重的银饰压得脖颈发酸。合卺酒喝下去像吞刀子,复株累忽然按住她的手,年轻人掌心滚烫:“我知道你恨我。”王昭君抬头,看见这个二十二岁的新单于眼里有和自己一样的惶恐。他继续说:“可我若不按规矩娶你,其他部族首领就会来讨要汉朝公主。到时候你要去的帐篷,可能连一扇朝南的窗户都没有。”帐外传来守夜人苍凉的牧歌,王昭君闭上眼,想起老单于临终前拉着她和复株累的手叠在一起,枯瘦的指节硌得人生疼。原来所有人都明白这场棋该怎么走,只有她还抱着那点长安带来的倔强。 草原上的女人活得像牧草,风往哪吹就往哪倒。第二年春天王昭君生下第一个女儿时,帐外传来汉使求见的消息。她抱着婴孩的手紧了紧,复株累看她一眼,忽然说:“你若想见,我陪你一起。”来的是位年轻使臣,捧着汉帝赏赐的锦缎珠宝,眼睛却总往她怀里婴儿身上瞟。王昭君挺直脊背,用最标准的长安官话谢恩,每个字都像在舌尖打磨过。等使者退出大帐,她后背的衣裳汗湿一片。复株累掀帘进来,默默递过一碗温好的马奶:“孩子像你,眼睛亮。” 或许日子就是这样熬成习惯的。她教复株累写汉字,他带她在盛夏去北海骑马;她生下第二个女儿那天,他竟从三百里外猎回一头白鹿,说这是长生天赐的吉兆。有次女儿们玩闹着问:“阿母为什么总爱看南方?”王昭君怔了怔,复株累抱起小女儿高高举起:“因为南边有太阳,咱们草原的鸿雁啊,心里永远揣着暖和地方。”那一刻王昭君忽然鼻子发酸,这个曾经莽撞闯进她帐篷的年轻人,什么时候学会了把她的乡愁编成童话讲给孩子听? 史书只会记下“王昭君,字嫱,南郡人。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后嫁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从其俗嫁复株累单于,生二女”。短短四十字,压着一个人二十年。没人问过她是否愿意,就像没人问草原愿不愿意每年被风雪剥掉一层草皮。那些长安城茶馆里摇头晃脑的文人,大概还会赞叹“昭君出塞”的深明大义,仿佛女子的人生只是史册里添彩的注脚。 其实哪有什么深明大义,不过是在命运给的窄路上,努力走出最像人的样子。她没做成从一而终的汉家贞女,也没成为宁死不屈的烈女子,只是活着,在异乡的帐篷里生下两个孩子,在琵琶曲里藏一点故乡的月光。或许所谓和亲,从来不是公主嫁给单于那么简单,而是让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一个人血肉之躯里找到某种笨拙的共存方式。 王昭君病逝那年草原大旱,据说送葬的队伍走了三天,沿途部落都有人跪拜。她的墓碑朝南,复株累亲手刻的汉字有些歪斜:“汉家明月,草原春风”。很多年后,牧民们还会指着天边南飞的雁阵说,看,那是昭君阏氏回娘家省亲去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