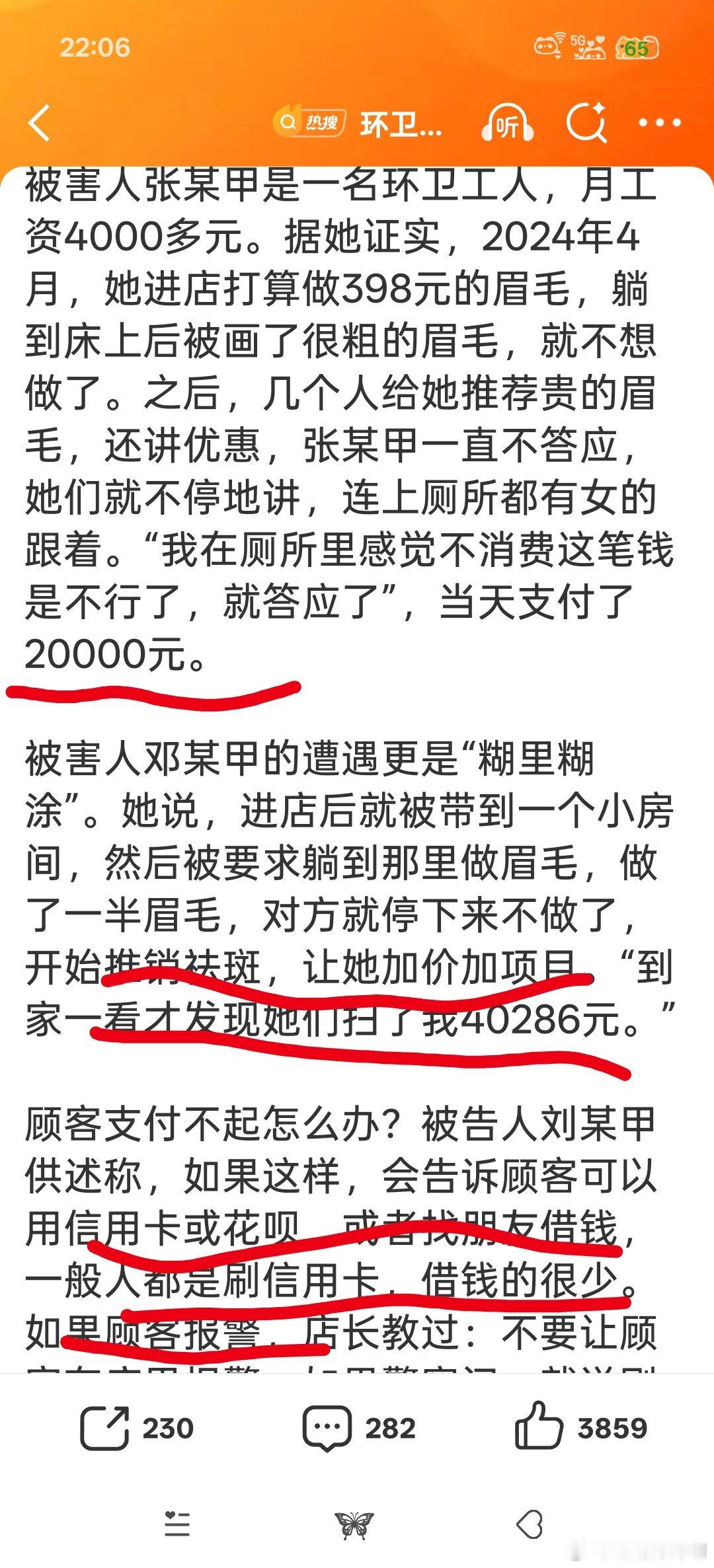1960年,北大教授张文裕icon回家后,发现妻子王承书icon留下“祖国需要我”的字条后失踪,这一分别便是17年。 张文裕捏着那张薄薄的字条,指腹摩挲着“祖国需要我”五个娟秀却坚定的字迹,客厅里还留着王承书早上煮的粥的余温,沙发上搭着她没织完的毛线袜,书桌一角放着半本摊开的核物理专著,可那个朝夕相伴的人,却悄无声息地不见了踪影。他没有慌着呼喊,没有四处寻觅,只是缓缓坐在沙发上,眼眶泛红,喉结滚动着说不出一句话——作为与妻子并肩归国的爱国科学家,他比谁都清楚,这五个字背后,是不容迟疑的使命,是隐姓埋名的坚守,是以身许国的决绝,这一去,不知归期,甚至不知能否再相见。 张文裕与王承书,本是留美学界的一对璧人,更是骨子里刻着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1936年,王承书远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核物理,成为该校物理系首位女博士,凭借在气体分子运动论、核裂变理论上的卓越研究,被美国学界誉为“核物理领域的明珠”,手握终身教职和优渥待遇;张文裕则深耕粒子物理,是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在美国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宽敞的别墅,还有着旁人艳羡的科研条件。可抗战胜利后,看着祖国百废待兴、被列强技术封锁,两人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一切,于1956年冲破重重阻碍归国——他们拒绝了美国学界的挽留,放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只为一句“祖国需要我们”,只想用毕生所学,为新中国的科技崛起铺路。 回国后,张文裕受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一边培养物理人才,一边深耕科研;王承书则进入原子能研究所,投身核物理基础研究,夫妻俩相濡以沫,白天各自忙碌,夜里灯下并肩探讨学术,日子清贫却充实。可他们心里都清楚,新中国的核工业刚刚起步,面对美苏的核垄断和技术封锁,想要打破“无核则弱、无核则欺”的困境,研制出氢弹,急需顶尖核物理人才投身其中,而这项任务,涉密、艰苦,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更不能告知家人。 1960年,国家秘密启动氢弹研制工程,王承书因在核裂变、核聚变理论上的深厚造诣,被邓稼先等核心科研人员点名,成为氢弹研制团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专家。接到任务的那一刻,王承书没有丝毫犹豫,却陷入了两难——她舍不得相伴多年的丈夫,舍不得年幼的孩子,可祖国的召唤,她无法拒绝。最终,她没有当面告别,只是写下“祖国需要我”五个字,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悄悄奔赴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从此隐姓埋名,消失在所有人的视野里,包括她最亲近的家人。 张文裕很快便读懂了妻子的心意。他知道,王承书不是不爱这个家,而是比起小家的团圆,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底气,更让她放不下;他也清楚,以妻子的性子,一旦接下任务,就会拼尽全力,哪怕付出一切,哪怕长久分离。从那天起,张文裕收起了思念与不舍,一边照常在北大授课,悉心培养学生,一边独自拉扯孩子,操持家务,将所有的牵挂,都藏在深夜的灯光里——他会时常翻看王承书的照片,摩挲她留下的专著,哪怕没有一句消息,哪怕不知道妻子身在何方、是否安好,他也从未抱怨,从未放弃等待,因为他坚信,妻子正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件能让祖国挺直腰杆的大事。 而远在戈壁滩的王承书,正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甚至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和温暖的住房,她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住在简陋的土坯房里,顶着戈壁滩的狂风烈日,靠着算盘、草稿纸,日夜不停地推演氢弹理论数据。核物理研究本就精密,一丝差错便会导致满盘皆输,再加上国外技术封锁,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王承书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累了就趴在桌上歇一会儿,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哪怕患上严重的胃病,哪怕头发渐渐花白,她也从未停下脚步。 她不能给家人写信,不能给家人打电话,甚至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行踪,每天面对的,只有密密麻麻的数据、反复失败的实验,还有深入骨髓的孤独。可每当她疲惫不堪、想要退缩时,“祖国需要我”这五个字,就会在她脑海里浮现,支撑着她咬牙坚持——她知道,只要氢弹研制成功,中国就能打破核垄断,就能不再受列强的讹诈,就能让亿万同胞过上安稳的日子,这份信念,足以让她克服所有艰难险阻。 这一分别,便是17年。17年间,张文裕从青丝熬到了白发,孩子从懵懂孩童长成了青年,他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教书育人,深耕科研,用自己的方式,支援着祖国的建设;17年间,王承书参与完成了氢弹理论设计的关键工作,见证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辉煌时刻,看着蘑菇云在戈壁滩升起,她泪流满面,所有的艰辛与孤独,都在那一刻有了意义。 1977年,随着氢弹研制任务的逐步完成,涉密等级降低,王承书终于得以脱下“隐身衣”,回到了北京的家中。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她看着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张文裕,看着早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张文裕看着眼前的妻子,她比离开时苍老了太多,眼角布满皱纹,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