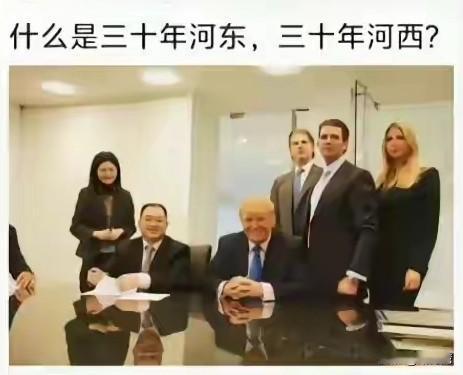1952年秋,齐白石快90岁了,背有点驼,却突然来了劲,拽着25岁的新凤霞进了里屋。 屋里木柜沉得很,黄铜锁扣磨得发亮,拉开时“咔嗒”一声,码得整整齐齐的银元、纸币直晃眼。 他指着柜子喘着气:“随便拿,要多少拿多少。” 新凤霞手指攥着衣角,轻声却没打颤:“干爹,我是来学本事的,不是来拿钱的。” 老人盯着她看了半晌,突然笑了,背着手往外走:“这孩子,懂规矩。” 那以后,她每周都骑着二八大杠穿胡同,车筐里总装着刚蒸的糖包,给干爹当早点。 齐白石教她画虾,笔锋在宣纸上一挑,墨色浓淡里就像有虾在游,她盯着看,连呼吸都放轻了。 有回她临摹的虾尾巴歪了,老人却笑出了声:“活的!这虾是刚从河里捞上来的!” 后来他还让她翻那些锁在樟木箱里的画稿,黄纸都发脆了,边边角角小心地用浆糊粘过。 1957年冬天,齐白石走了。 新凤霞和吴祖光没能去送葬,站在胡同口,风卷着雪片子往脖子里钻,眼泪刚流出来就冻成了冰碴。 没过多久,批斗会一场接一场,有人踹她膝盖,“咔嚓”一声响,她抱着腿在地上滚,心里却猛地想起干爹画的虾——那么软的身子,怎么就挣得出网呢? 她被关在小屋里,墙皮掉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黄土。 左腿肿得穿不上棉裤,可夜里闭上眼,宣纸上的虾又活了,须子在眼前飘。 她咬着牙想:“艺术还在,就不能倒。” 1975年脑溢血后,右半边身子动不了,说话也费劲,有人说:“新凤霞这下彻底完了。” 她却让丈夫把画板架在轮椅上,用还能动的右手攥紧狼毫,墨汁滴在宣纸上,晕开个小墨点,像极了当年学画时滴的第一滴。 她画的牡丹不像旁人那样艳,花瓣总带着点颤巍巍的劲儿,倒像是寒风里刚绽开的。 丈夫吴祖光握着她的手教写字,“一”字写得歪歪扭扭,铅笔尖断了好几次。 后来她写出几百万字,书里写被踹断腿那天的月光,写齐白石教她调颜料时说“颜色要活,跟唱戏一样,得有精气神”。 有人问她苦不苦,她指着手边的画:“你看这虾,断了须子也能游。” 那柜子里的钱她从没碰过,可那份“随便拿”的信任,比银元还沉。 后来她总在画里题一句:“干爹说,艺术是地里的种子,埋多深都能发芽。” 现在看她的画,墨色里不光有花鸟虫鱼,还有个姑娘咬着牙,把断了的翅膀,又绣成了新的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