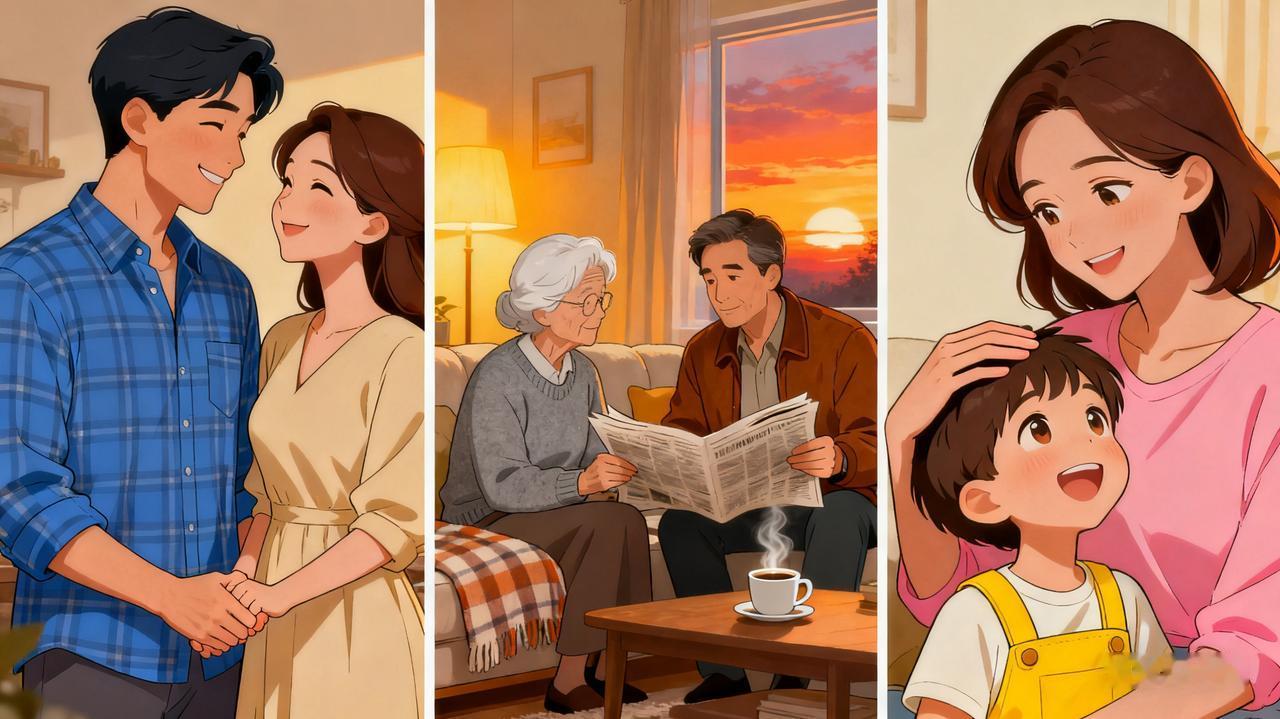刘震云说:“世上最危险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至亲至疏是夫妻。爱时亲密无间,恨时互相伤害。夫妻之间没有血缘,任何形式的爱,都需要条件和利益。”
刘震云先生关于夫妻关系的解读,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亲密关系里最复杂的光。他笔下的“危险”与“张力”,其实早被无数过来人印证——
钱钟书在《围城》里写:“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这“进”与“出”的拉扯,恰是夫妻关系的常态:爱时恨不得融成一体,怨时又巴不得划清界限。
就像两棵并肩的树,根在地下缠绕,叶在风中碰撞,既共享阳光,也分担风雨,这大概就是三毛说的“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
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亲密却独立,依赖又自由。
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相似”里藏着的,或许就是对“至亲至疏”的默契平衡。爱到浓时,如杨绛与钱钟书“我们仨”的温情,她懂他伏案写作的专注,他惜她操持家务的琐碎,连拌嘴都带着“不要紧”的包容。
怨到深处,又可能像张爱玲笔下的《金锁记》,曾经的依恋变成最锋利的刀,因为“他见过你最真的模样,所以最知道哪里捅下去最疼”。
但就像蒙田说的:“美满的婚姻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一,不幸的婚姻则是人生最大的磨难。”这磨难里其实藏着成长。那些在争吵后摔门而去,却在楼下买了对方爱吃的早餐回来的瞬间;那些记得彼此过敏的食物、藏在枕头下的降压药、深夜悄悄掖好的被角的细节,都是在“危险”里生出的韧性。
就像老话说的“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这份没有血缘的羁绊,本就是一场需要用耐心、智慧和一点点“难得糊涂”去经营的修行。
最终,能走过漫长岁月的夫妻,大抵都懂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放在夫妻关系里,便是在看清彼此的棱角、接纳无数次“至亲至疏”的摇摆后,依然愿意为对方添一杯温水,在清晨的阳光里说一句“今天也要好好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