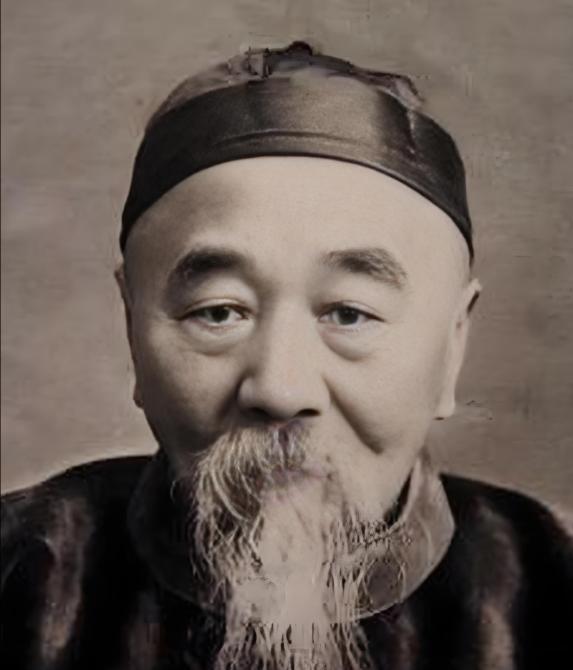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是个大贪官,一生收受贿赂无数,他搞贪腐有一个特点,绝不让送钱的人吃亏,因而在官场获得了“取之有道”的美誉,一生无人检举告发 有人弹劾李瀚章,说他贪得无厌,收钱收得手都软,可调查组来了一圈,最后啥事没有。这种场面,老百姓看得明明白白,人人都知道他贪,可他偏偏安稳坐在高位,谁也奈何不了他。 别人贪污是明抢暗偷,李瀚章倒像开了个豪华会所,规则透明,明码标价,搞得一众同行都服气。把贪腐做成了生意,人人有份,个个得利,最后全社会都把规矩玩成了笑话。 李瀚章的能耐就在于把“取之有道”做到极致,他不是不贪,他是贪得有章法。钱送到他手里,送的人反而不亏,甚至觉得自己抄了近道。 他就是把权力变现做成了长期可持续的生意,谁也挑不出太大的毛病。可这样一来,整个官场的底线也就一点点被他拉低了。 李瀚章早年混迹于湖南,协办团练,办湘军后勤。那会儿军需供应的水有多深,他心里最清楚。军粮、军械、被服,每一笔都能生出无数油水。那些年他学会了人情世故,但那时的手法还比较直接。 等到调任四川总督,要路过彭山县,他的胃口开始变大了。灰鼠皮帐盖,燕窝,都是当时的奢侈品,县里的财政本就捉襟见肘,彭山县令听说要送这些东西,直接在县衙里急得掉眼泪,死活拿不出这么多好货。可架不住上级的压力,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把银钱凑齐,算是“打发”了这位过路的总督。 李瀚章摆明了是“过境勒索”,县令一边掉眼泪,一边还得想办法把事摆平。李瀚章也不是没看出来,这种光天化日下伸手要钱的做法,风险太大,吃相太难看。 早年的李瀚章,出手粗暴,权力刚上手,没学会怎么优雅地收钱。彭山这一遭,他心里其实也有点发虚。后来回头再看,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既容易留下把柄,也搞得自己没脸面。他开始琢磨怎么让贪腐看起来没那么扎眼,既能长久,又能让送钱的人心甘情愿。 时间一长,李瀚章的手法越来越娴熟。他发现,送钱的官员和商人,其实都想要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比方说那个候补知县,想捞个汉阳知县的肥缺,送了两千两银子。李瀚章收钱不含糊,交代得也不含糊,提醒对方以后收厘金别下手太狠。 知县上任后,果然油水丰厚,几年后升了知府,反过来又送了五千两银子来感谢。这就是李瀚章的生意经,投资有回报,官场变成了稳赚的理财产品。做得好了,大家一起赚,做得差了,最多换个人接盘。 有一次,有个道台本来要去广东任职,李瀚章把人叫到自己屋里,语气温和地建议他改去江苏。钱已经收了,可他还替人着想,安排得妥妥帖帖。 道台被打点得服服帖帖,回去还帮他美言几句。李瀚章的人情世故,做得滴水不漏,既收了好处,又收了人心。外人看不出破绽,只觉得这位总督实在会做人。 其实,这种操作在当时并不罕见,《翁同龢日记》里也有不少类似的记载。官场上送礼成风,谁都明白这是一张无形的关系网。李瀚章的“高明”就在于,他把这一套玩得恰到好处,既不越线,又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所有的打点都在潜规则范围内,谁也挑不出太大问题。朝廷弹劾他,调查组最后只能无功而返,只能说“无实据可查”,反而让他越发安稳。 李瀚章从来不让送钱的人吃亏,这成了他的招牌。送钱的人觉得值,收钱的人觉得安全。李瀚章的“取之有道”,实则是把规矩当成了保护伞。只要不做得太过分,谁都不会主动捅破窗户纸,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晚清的官场,就是这样一潭死水。李瀚章这样的“高人”,把贪腐做成了合情合理的生意。大家看着他风光无限,其实都是自己人,李瀚章的“聪明”,成了这个时代最无声的讽刺。 主要信源:(《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李瀚章传》;安徽省志——《安徽省志·人物志·李瀚章》;人民网——李鸿章哥哥摆架子被下级痛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