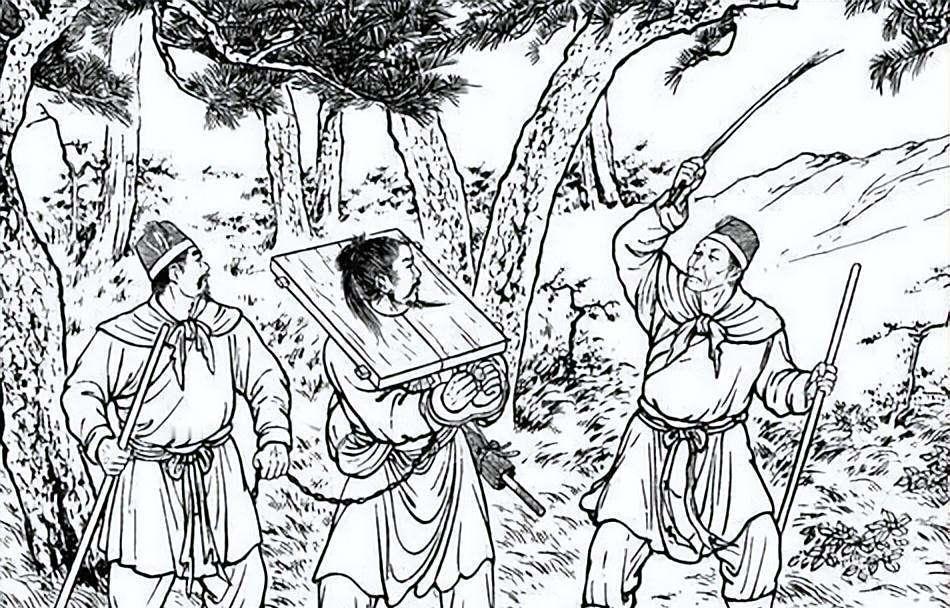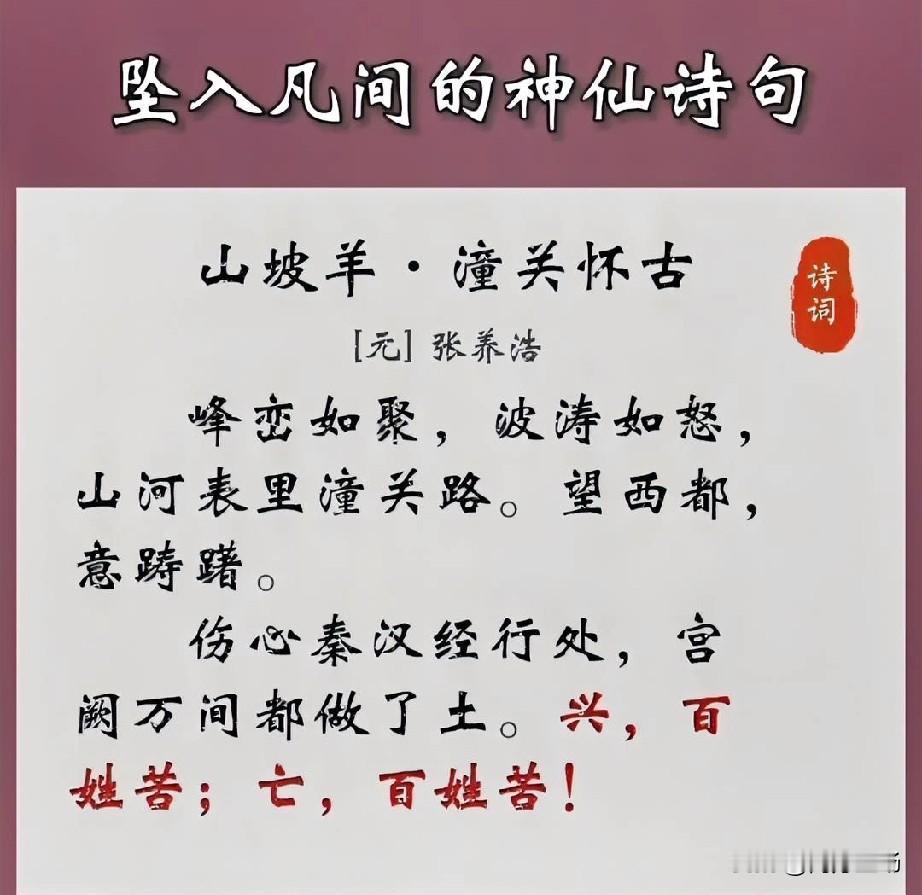苏联把犹太自治州建在黑龙江边,结果十六万人口,只有几千犹太人 1920年代末,苏联政府在民族政策上搞了个“大动作”,他们决定为境内犹太人设立一块专属的居住地。 彼时的苏联,犹太人口大约有200万,分布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多数生活在城市,靠商业、手工业维生。 但由于沙皇时期的反犹传统与革命后混乱的政策环境,这些犹太人在社会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为了“解决民族问题”,苏联想出了个方案:给犹太人划块地,让他们集中居住、自主发展,既能体现“民族平等”,又可以通过“安置”来减少他们在西部城市的影响。 苏联最终选址在远东的比罗比詹,一个地处黑龙江畔、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的偏远地区,这个地方几乎没有现代基础设施,气候严酷,冬天零下四五十度,夏天又湿热多虫。 但选择此处的目的是地广人稀,正好符合苏联政府的两个目标:开发边疆、巩固远东防线。 美国犹太人组织曾建议把自治区设在克里米亚或乌克兰南部,还表示愿意出资金援建,但斯大林不为所动,认为克里米亚民族太杂,容易引发冲突,而远东反而“干净”,最终,这块地被拍板定为“未来的犹太家园”。 第一批犹太移民从西部赶往比罗比詹时,迎接他们的是茫茫沼泽、简陋木棚和刺骨寒风,而不是梦想中的“新世界”,仅第一年,就有超过60%的移民选择离开。 这些犹太移民,大多没有种地经验,他们习惯于城市生活,精于手工艺、经商、教育等行业,结果到了比罗比詹,不会种田、不会伐木、不会过冬,生活极度艰难。 有历史学家形容:“他们不是被安排来生活的,而是被安排来‘生存’的。” 面对移民潮退,苏联开始加大宣传力度,甚至在美洲、阿根廷、德国等地招募愿意“参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犹太人。 1934年,比罗比詹正式升格为“犹太自治州”,成为苏联唯一一个以民族命名的州级行政区。 根据苏联官方统计,1937年犹太自治州的犹太人口达到顶峰,约有4万人,然而,即便在最鼎盛时,犹太人也只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大量非犹太族群,尤其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等,也被安置进来,进一步稀释了“民族自治”的成色。 1948年,以色列建国,成为全球犹太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一事件,直接削弱了比罗比詹的“象征价值”,过去还能说这里是苏联版的“犹太希望”,但以色列一出场,谁还会为比罗比詹买单? 冷战期间,苏联与以色列关系迅速恶化,犹太自治州开始被边缘化,政府投入减少,经济发展跟不上,年轻人纷纷外出求学、工作,犹太人口也逐年递减。 苏联解体后,局势更加动荡,大量犹太人趁机离开俄罗斯,前往以色列、美国或德国,截至2021年,犹太自治州总人口约16万人,其中犹太人仅剩837人,占比不到0.6%。 如今,当地大多数人是俄罗斯族,犹太文化只在少数教育和文化场所中得以保留,目前全州只有三所教授意第绪语的学校,但这些也只是文化意义上的“留影”,而非活跃的民族生活。 外界常常疑惑:以色列都在招人了,为什么还有人不走?其实这背后既有现实原因,也有情感牵绊。 比罗比詹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对一些年长的犹太人来说,这里就是家,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讲的是俄语和意第绪语,吃的是混合口味的俄式犹太菜,信仰也早已与传统犹太教有了距离。 他们不一定认同以色列的政治制度,也未必适应那里的社会生活。 历史学家瓦列里·古列维奇曾说:“犹太人的根在哪,‘应许之地’就在哪,不见得非在以色列。”对他们来说,比罗比詹也许不是理想国,但却是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这种文化残留的坚守,也是一种另类的民族认同,不是靠宗教仪式和语言保持身份,而是靠与土地的连接、与社区的关系来维系。 这场实验失败的根源,其实并不复杂:没有考虑文化适应,没有尊重传统生活方式,没有给人自由选择的空间,所有的“为你好”,如果不是出于理解,那就是强推。 犹太自治州的命运,也折射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当国家出于战略或政治需要,去设计民族命运时,往往忽略了个体的情感与归属,比罗比詹不是没人来过,而是没人愿意留下,不是因为这里不够大,而是因为心不在此。 2025年,这个犹太自治州仍然存在,名字还在用,地图上也能找到,但它早已不是犹太人的聚集地,而只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边远地区。 它像一页夹在历史书中的插图,证明曾经的理想主义也能被写进宪法,但不能写进人心,犹太人走了,留下的只是一些意第绪语的街头招牌、节日纪念日和博物馆展品。 它的存在,不再是为了“未来”,而更多是为了提醒人们:民族认同从来不是行政划分能解决的事,文化归属也不是搬家就能建立的根。 信息来源:犹太自治州2008年社会经济概况——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