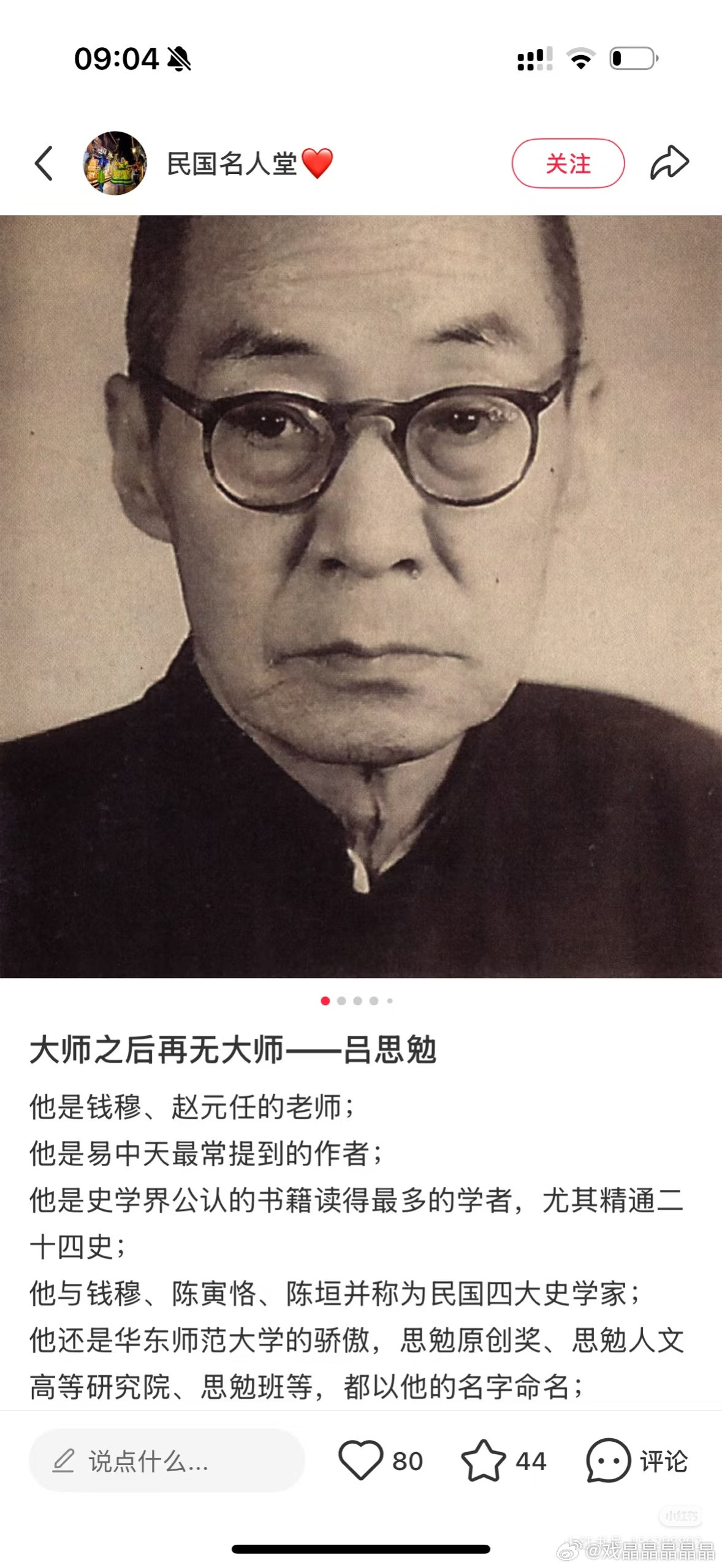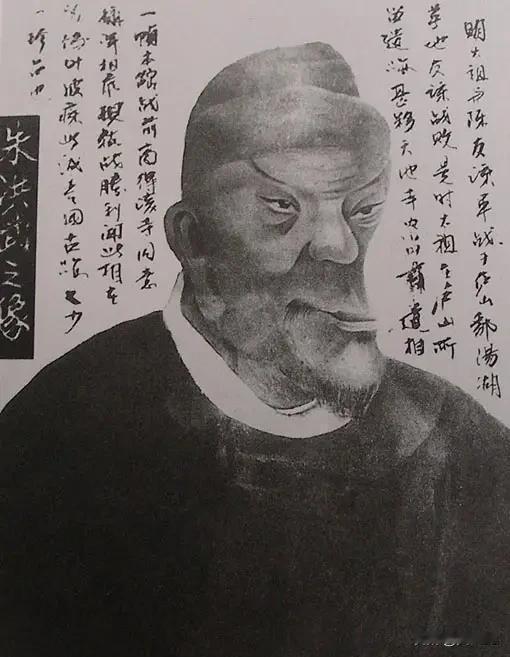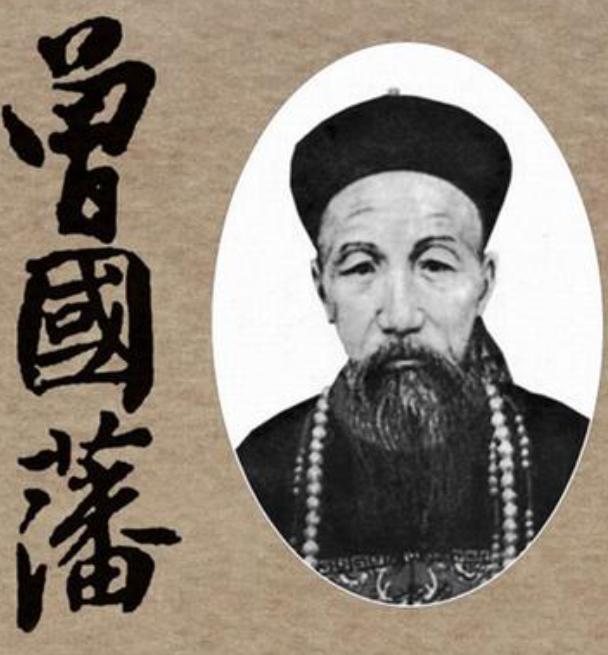在康熙眼中,这人不是好官,但在江南百姓心中,他被视为再生父母 康熙爷的朝堂上,总有些让他挠头的官员,陈鹏年就是其中一个——这位湖南汉子拿着朝廷的俸禄,却总干些“不把皇帝心思放第一位”的事,在康熙眼里,他犟得像块茅坑里的石头,不懂变通还爱惹麻烦,绝对算不上循规蹈矩的好官 可在江南百姓心里,他比亲爹还亲,修水利、减赋税、平冤狱,哪里有难处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说是再生父母都嫌不够贴切。 这俩评价差着十万八千里,根子就出在“当官为谁”的算盘上,康熙要的是朝堂安稳、官员听话,陈鹏年偏要把百姓的柴米油盐当头等大事,自然就成了皇帝眼里的“问题官”,百姓口中的“陈青天”。 陈鹏年刚踏入官场那会儿,就没按官场潜规则出牌。28岁中进士后,他先在浙江西安县当知县,一到任就把“清、慎、勤”三个大字贴在书房,不是摆样子给上司看,是真把这三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当时西安县的田赋混乱得一塌糊涂,贪官污吏借着田亩不清的由头,把赋税都摊到了穷苦百姓头上,不少人家被逼得卖儿卖女。换作别的官员,多半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事牵扯到地方豪强的利益,闹大了容易引火烧身。 可陈鹏年偏不,他带着衙役拿着旧田亩图册,顶着大太阳在田埂上跑了三个月,一块地一块地核实归属,把那些被豪强侵占的田产一一厘清,按实际田亩收税。 就这一件事,让数千农户保住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不用再为苛捐杂税发愁。他还在县城东门外修了座分水闸,干旱时开闸放水灌溉农田,百姓干脆把这闸叫做“陈公闸”,至今还能找到当年的遗迹。 可这事传到上级耳朵里,却成了“擅动地方旧制”的小辫子,康熙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时,大概率是伴随着“不懂官场规矩”的评价。 真正让康熙对他皱紧眉头的,是他在江南的任职经历。康熙四十一年,陈鹏年被调到山阳当知县,这里刚遭过水灾,田地全被淹了,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户部却催着追缴之前的欠赋。 按朝廷规矩,官员得无条件执行户部指令,可陈鹏年看着沿街乞讨的灾民,直接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税。这封奏折递上去,康熙心里能痛快才怪——在他看来,官员首要的是维护朝廷权威,哪能动不动就为百姓跟朝廷讨价还价? 可陈鹏年根本没管皇帝的脸色,一边上书一边开仓放粮,还组织百姓兴修水利,没过多久就把山阳从泽国变成了粮仓,百姓门上都贴着“官清民安”四个大字。 等他调任海州时,山阳百姓拦着路不让走,哭着往他车里塞自家种的粮食,这场景要是被康熙看到,估计又要骂他“收买民心”。 康熙四十七年,陈鹏年升任苏州知府,这下彻底把“麻烦”惹大了。苏州是江南富庶之地,也是权贵聚集的地方,时任两江总督噶礼在这儿一手遮天,贪污受贿、欺压百姓没人敢管。 陈鹏年到任第一天,就在府署大门上写了“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八个字,相当于把“我要跟恶势力对着干”写在了脸上。他先清理积案,一个月就处理了三百多件压了好几年的案子,其中不少是噶礼亲信犯的事;接着又整治漕运弊政,断了噶礼的财路。 噶礼哪能忍,立马罗织罪名弹劾他,说他在修演武厅时“大不敬”,把康熙的御笔题词随便摆放。康熙本来就觉得陈鹏年“刺头”,加上噶礼在旁边煽风点火,当即下旨把陈鹏年革职查办,差点砍了他的头。 可康熙没想到,圣旨刚到苏州,百姓就炸了锅。当时苏州正闹水灾加疫病,陈鹏年一边组织人挖渠排水,一边设了十几个医局免费给百姓治病,还自己掏腰包买药,家里八十岁的老母亲跟着他吃糠咽菜,住处空得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百姓听说他要被问斩,上万人生拉硬拽把押解他的囚车拦住,还有商户主动罢市请愿,跪在总督府门前喊冤。甚至有文人写了《陈太守再生记》,把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 康熙接到奏报后愣住了,他实在想不通,这个“不听话”的官员,怎么就这么受百姓待见? 其实答案很简单,康熙坐在金銮殿里看的是奏折,百姓站在田埂上看的是实绩——陈鹏年在苏州期间,光是治水就救活了数万百姓,设医局救治的病人不计其数,而噶礼这样的“听话官”,只会吸百姓的血。 直到陈鹏年去世后,康熙才慢慢明白,这个让他头疼的官员,从来没为自己谋过一点私利。他在西安时,百姓在烂柯山上为他建祠,每年他的生日都凑钱庆祝,叫“陈公会” 在江宁、山阳等地,百姓也纷纷立祠祭祀他,把他的牌位供在自家祠堂里。而那些康熙眼里的“好官”,比如噶礼,后来因贪污被抄家,百姓放鞭炮庆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说白了,康熙和江南百姓的评价差异,本质上是立场不同。康熙要的是能维护皇权、遵守规矩的官员,陈鹏年却把“百姓的事比天大”刻在心里,宁可违抗圣旨也要保百姓平安,自然成了皇帝眼里的“问题官”。 这样的官员,康熙或许到死都没完全认可,但江南百姓用立生祠、写民谣的方式,给了他最公正的评价——那些被皇帝误解的“不是好官”的特质,恰恰是百姓最需要的“父母官”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