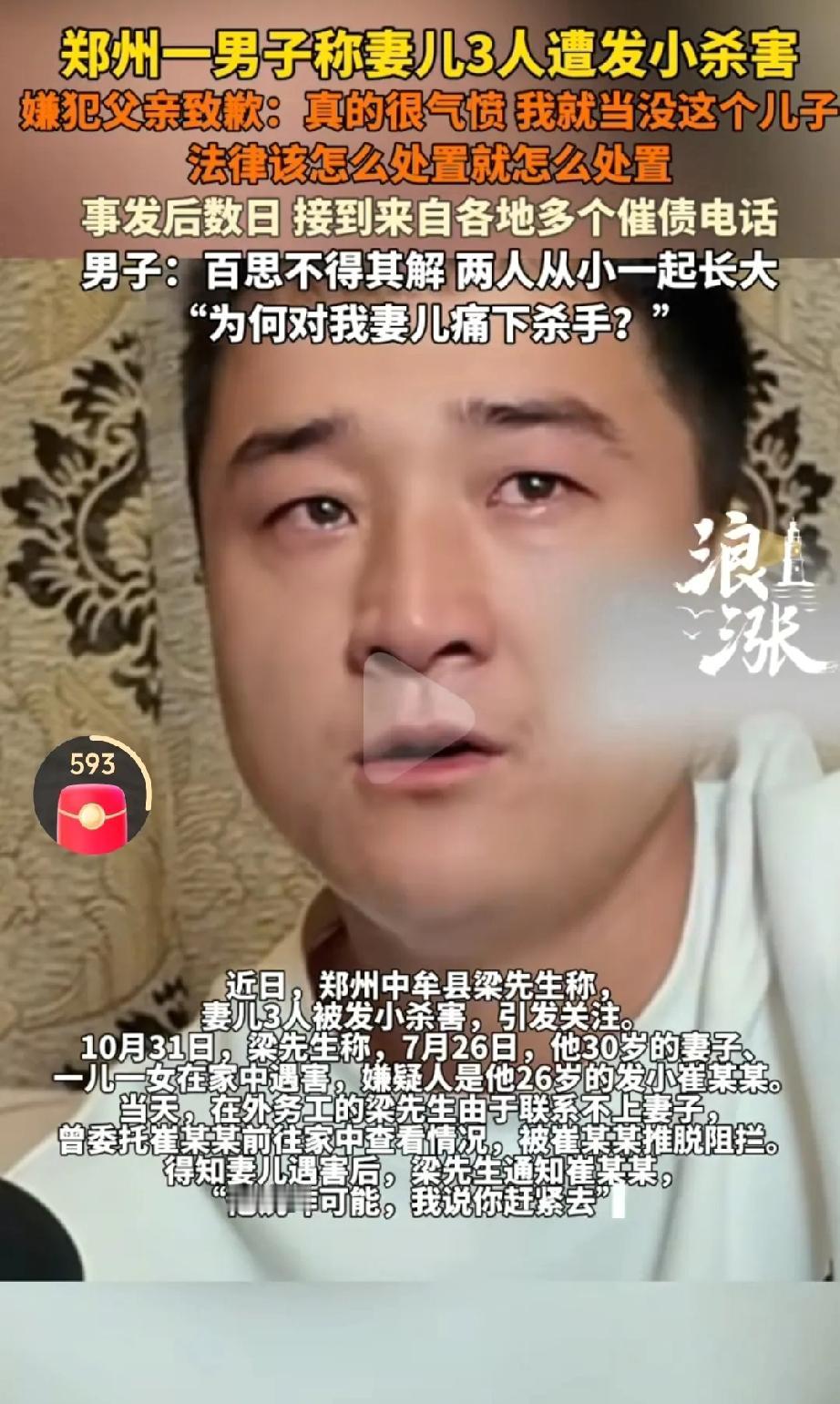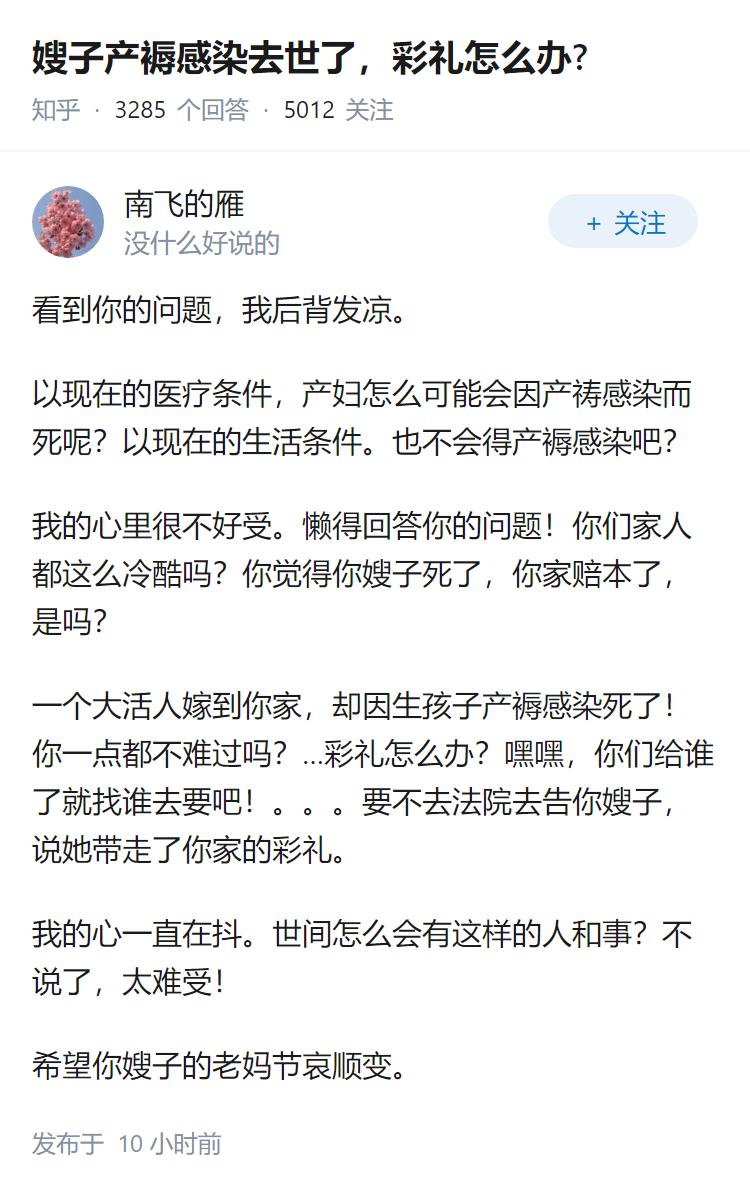1970年,陈独秀58岁的女儿陈子美身绑5个空油桶,带着小儿子偷渡香港,9个小时后,母子俩奇迹般抵达目的地,哪知,刚上岸,就遇到警察,陈子美很是沮丧,不料,警察的举动让她大感意外。 1970 年珠江口夜色中,58 岁的陈子美身绑 5 个空油桶,带着小儿子在浪里漂浮。 9 小时后爬上海港滩头,刚喘口气就撞见巡逻警察,她心一沉:“这下完了。” 可警察没盘问,反倒递来干衣服和热水,这意外的善意让她红了眼眶。 指尖触到杯壁的温热,她忽然想起父亲陈独秀早年教她写的毛笔字。 1912 年出生上海,父亲总在书房写文章到深夜,偶尔会教她认 “自立” 二字。 那时他还没全身心投入革命,睡前会给她讲古籍里的女子故事,眼神温和。 后来家里常客渐多,谈的都是家国大事,父女间的闲谈慢慢少了。 1925 年父母分开时,她才 13 岁,跟着母亲高君曼搬到南京草屋。 父亲每月寄 30 块大洋,信封里从无只言片语,母亲说 “他心里装着更大的事”。 她夜里缝补衣服时,总想起从前父亲把银元放桌上说 “念书靠自己” 的模样。 那份疏离感,让她早早明白,父亲的世界里,家人从不是重心。 1931 年母亲病逝,19 岁的她攥着父亲寄来的钱,连丧葬费都不够。 她没敢给狱中的父亲写信报丧,听说他因政治问题被捕,处境艰难。 后来托人带话,只说自己在学妇产科,父亲托人回了句 “手艺能安身”。 没有安慰,只有务实的叮嘱,这符合她对父亲一贯的认知。 1932 年她带着男友张国祥去探监,想征求父亲对婚事的意见。 陈独秀盯着张国祥看了许久,直言 “这人靠不住,你太年轻看不透”。 她当时觉得父亲固执,没听劝,执意结婚,后来才懂父亲的识人眼光。 那次见面,父亲塞给她一本《本草纲目》,说 “接生多懂医理没坏处”。 抗战逃难途中,她怀里总揣着那本《本草纲目》,书页被雨水泡得发皱。 听说父亲在重庆江津生活困窘,她托人送去自己攒的微薄薪水,却被退回。 附信说 “我自有生计,你顾好自己和孩子”,语气依旧硬朗。 她望着战火中的天空,忽然理解了父亲骨子里的骄傲与倔强。 1942 年父亲病逝,她在上海助产士诊所里接到消息,正在给产妇接生。 忙完手头的活,她躲在杂物间哭了一场,手里还攥着沾着血的纱布。 她没去奔丧,一来路途遥远,二来家里五个孩子等着吃饭,实在走不开。 后来才知道,父亲临终前曾问起她,说 “小美那孩子,手巧能吃苦”。 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父亲的 “身份” 成了她的包袱,批判标语贴满家门。 第二任丈夫李焕照因此离婚,她对着空屋,第一次怨过父亲带来的牵连。 可看到床头那本《本草纲目》,怨气又淡了 —— 那是父亲留给她唯一的念想。 她知道,父亲从未想过拖累家人,只是命运弄人。 1970 年偷渡前,她把《本草纲目》缝进小儿子的棉袄夹层里。 漂在海上时,想起父亲一生漂泊,从新文化运动到晚年隐居,从未安稳。 或许是血脉里的韧劲,支撑着她在浪涛中坚持了 9 小时,没被打垮。 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和父亲,都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人。 在香港重操旧业时,她常给产妇讲父亲当年教她的医理知识。 1975 年移民美国,那本《本草纲目》成了她行李箱里最珍贵的物品。 有人问起她的父亲,她只淡淡说 “是个写文章的老人”,不愿多提。 那份复杂的情感,有怨有敬,更多的是无法言说的羁绊。 她曾忍痛将与张国祥所生的四个子女托给亲戚,后来子女们多在大陆生活。 2004 年冬天,93 岁的陈子美在纽约医院安静离世。 遗体在太平间放了一个多月,直到外孙李大可在领事馆帮助下赶来。 李大可按照遗愿,给她穿上当年的嫁衣下葬。 陈子美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的两个女儿,曾因得知母亲消息寻求联系,却终未见面。 随行的小儿子自 1991 年离去后,便再无公开音讯,成了她晚年未解的牵挂。 这位陈独秀的女儿,一生与父亲聚少离多,与子女亦多有隔阂,最终在异国长眠,只留下一段被时代裹挟的亲情往事。 信息来源:环球网《陈独秀之女的坎坷人生:绑汽油桶偷渡香港》 中华网《陈独秀女儿陈子美一生坎坷:1970年突然失踪,原来是泅渡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