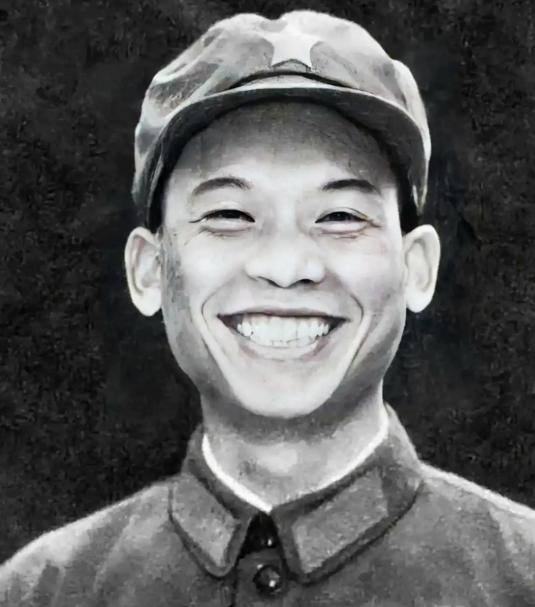1979年,我军一名走失的战士正在越南的农田里挖红薯,突然被人用石头砸了一下,小战士扭头看去,只见四名越军出现在眼前...... 1979 年 3 月的那个清晨,陈书利躲在田埂下的水沟里,牙齿咬得咯咯响。 四名越军举着枪在红薯地里搜,皮鞋踩过藤蔓的声音离他越来越近。 前一晚他刚从山洞里出来,肚子饿得发慌,才冒险来挖红薯充饥。 “当时我手里只剩半截刺刀,连枪都在突围时丢了。” 陈书利喝了口茶,接着说。 他想起那天雾特别浓,能见度不足十米,这成了他唯一的掩护。 越军的石头砸中他后脑勺时,他第一反应不是疼,是把红薯往水里藏。 “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在这,不然战友们的突围路线可能暴露。” 这段遭遇,要从三天前的大雾说起。 当时陈书利跟着 41 军执行穿插任务,要断越军高平退路。 浓雾裹住丛林时,他正扶着腿伤的战友李建国走在队伍末尾。 一阵越军冷枪袭来,队伍瞬间乱了,等枪声停了,他和战友已隔了片竹林。 “我喊了半天没人应,正慌着呢,就听见有人哼唧。 ” 陈书利转头看向身旁的刘志强。 当时刘志强正抱着胳膊流血的王建军,另外三个战友也围着伤员蹲在地上。 七个人凑到一起,才发现指北针坏了,三支冲锋枪里只剩两百多发子弹。 “书利,你读过书,你拿主意!”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大家的目光都聚过来。 陈书利没推辞,却没直接说往哪走,而是先帮伤员包扎。 “当时王建军腿上的血把裤子都浸透了,我把绑腿拆了给他勒紧。” 他想起老家老人说 “向北走总没错”,就跟大家约定: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突围。 可没走两里地,就撞见越军的巡逻队,七人赶紧躲进三间 “品” 字形木屋。 “那木屋堆的化肥袋救了我们命,我让大家把袋子垒成半人高的墙。” 陈书利记得特别清楚,越军第一次进攻时,他让战友等敌人到五十米内再开枪。 “李建国枪法准,第一枪就撂倒个扛机枪的,咱们才喘了口气。” 可没过多久,越军的迫击炮就来了,屋顶的茅草被炸得满天飞。 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个越南老太太的哭声,说她孙子被炮弹炸伤了。 陈书利犹豫了一下,还是让刘志强带着急救包出去看看。 “后来才知道,老太太是附近村民,不是越军的人,她还偷偷给我们指了条小路。” 这个小插曲,成了残酷战斗里少有的温暖记忆,后来他总跟人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 天黑后弹药快没了,陈书利决定分头突围,自己引开敌人。 “我往反方向跑时,听见战友喊我名字,可我不敢回头,一回头就全完了。” 跑了不知多久,他摔进个土坑,晕了过去,醒来时天已经亮了。 身上的干粮袋早丢了,只能在山林里找野果,直到看见那片红薯地。 “越军的石头砸过来时,我滚进水沟,憋着气不敢动。” 等越军靠近,他突然窜出去,凭着在部队练的格斗术夺下一把枪。 “我没开枪,怕引来更多人,就朝着竹林跑,雾大,他们没追上。” 又走了一天,听见熟悉的军号声,他才知道自己终于要回到部队了。 战后,陈书利退伍回了老家,在镇上当了名邮递员,一干就是三十年。 “我送信时遇到过不少老兵,后来就牵头组织了个老兵互助小组。” 他用自己的抚恤金帮困难老兵修房子,还帮牺牲战友的家属寻亲。 “当年我们没丢一个兄弟,现在也不能丢了他们的家人。” 如今,他的孙子也参了军,每次视频,他都要叮嘱 “要护着战友,别逞能”。 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军功章上,闪着淡淡的光,像在诉说那段难忘的岁月。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纪念馆的展柜里,那把当年用过的冲锋枪依旧陈列着。 主要信源:(《生死28天》)(《威震峡谷七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