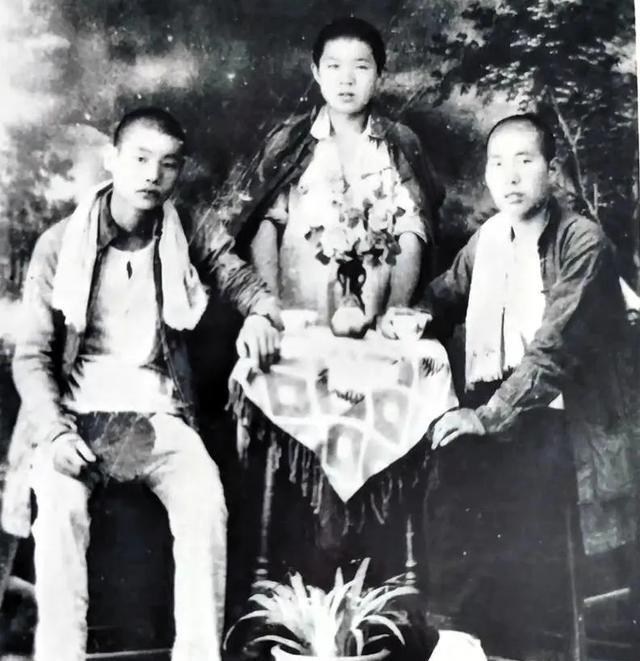1945年,八路军在公路上伏击日军,由于敌人太多,排长便下令撤退。一个小战士却因瞄准的太投入没听到,眼瞅日军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小战士低声问道:“排长,鬼子上来了,我开枪了!” 1944年8月的山东莒县,一个叫下崖村的地方。天儿闷得跟要下刀子似的,咱们八路军一个排的兄弟们,在高坡上趴了大半天,就为了等路过的日伪军,打个伏击。 计划本来挺好,情报说敌人就一个加强班,撑死五十来号人。咱们这边一个排,火力集中点,打完就撤,利利索索。可人算不如天算,临到头了,侦察兵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话都说不利索了:“排长,不对,不是五十个,是三百多个!主力是鬼子,伪军在前头探路!” 三百多对一个排,装备还不如人家。这仗怎么打?排长也是个明白人,当机立断,手一挥,压低声音吼道:“撤!快,悄悄地走,别惊动了!” 命令一下,大家伙儿心里再不甘,也只能猫着腰,一个跟着一个往后挪。战场上,命令就是天,硬拼那是傻。 可偏偏,就有人没听见。 这人叫赵友金,十六岁,刚入伍没多久的新兵。此刻的他,正透过准星死死盯着越来越近的鬼子,耳朵里全是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山里的风声一搅和,排长的命令愣是没钻进他耳朵里。 这孩子啥来头?他爹和他叔都是老革命,他从小就不是玩泥巴长大的,是摸着红缨枪,帮着大人站岗放哨长大的。所以他一到参军的年纪,二话不说就来了部队。 一开始,领导看他个头小,让他当通信员。可这小子一门心思要上阵杀鬼子,天天缠着班长,一有空就抱着枪练瞄准,练的还是不装子弹的“干练”。班长被他磨得没法,开玩笑说:“你小子啥时候枪法顺溜了,就让你进战斗班。”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友金把这话当圣旨了。他从小就跟着大人在山里打猎,对枪有种天生的感觉。等他第一次实弹打靶,老兵们都惊了。这小子,稳得不像个新兵。 第一次上战场,班长给了他十发子弹,千叮万嘱:“子弹比命金贵,没十足把握不准开枪!” 结果,战斗结束,赵友金十发子弹,干掉了四个鬼子,还撂倒俩,这战绩,在当时简直是神了。要知道,根据一些战后统计,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敌后战场,我们平均要用十几发子弹才能换掉一个敌人。 可也因为这“省子弹”的命令,他挨过一次批。另一场战斗,班长弹药打光了,让他火力掩护,他半天不开一枪。班长急了,吼他,他才委屈地挤出一句:“班长,我还没把握一枪一个……”气得班长抢了他的枪,硬逼着他打。结果剩下的六发子弹,他又干掉俩,伤了一个。 事后开会,排长点名批评他,说他死脑筋,不懂战场变通。赵友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当场就哭了,顶了一句:“不是说好了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吗?” 这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是啊,命令是这么下的,可现实又是另一码事。 说回到这次伏击。等赵友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准备请示开火时,他才纳闷了。他低声喊:“排长,鬼子上来了,我开枪了!” 没人回答。 他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他悄悄回头一看,我的天,阵地上空荡荡的,战友们一个都不见了! 这时候,一般人早就慌了,要么赶紧跑,要么吓得腿软。可赵友金这小子,脑回路不一样。他第一反应不是怕,而是明白了:我被落下了,那这仗,就得我一个人打。 他没跑。他把身子缩得更低,看着伪军大摇大摆地从山下走过去,他一枪没放。他知道,打这些二鬼子没用,得敲掉主心骨。等后面穿着黄呢子军服的鬼子大摇大擺地进入了他的射程,他一眼就锁定了队伍里那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 就是他了! 深吸一口气,稳稳瞄准,“砰!”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山谷的宁静。马上的鬼子军官一头栽了下来。 三百多人的队伍,瞬间炸了锅。指挥官没了,士兵们跟没头苍蝇一样四处找掩护。赵友金没给他们反应时间,迅速拉动枪栓,瞄准另一个鬼子机枪手,又是“砰”的一枪。 三百多人的日伪军,就因为一个新兵,彻底乱了章法! 鬼子不知道山坡上到底埋伏了多少人,只觉得子弹神出鬼没。赵友金打完两枪,看目的达到了,也不恋战,抱着枪就地一滚,顺着熟悉的地形,像个泥鳅一样溜下了山坡,钻进了林子里。 等他气喘吁吁地追上大部队,班长一把就抱住了他,眼睛都红了,反复就说一句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这一次,没人批评他,也没人表扬他。赵友金自己也明白了,战场上,神枪法很重要,但听命令,和战友们在一起,更重要。 赵友金是幸运的,他活了下来。他的那两枪,改变了一场小规模战斗的走向,也让他自己完成了从一个“倔强新兵”到“真正战士”的蜕变。他让我们看到,英雄,并不总是那些高大伟岸的身影,也可能是一个会因为委屈而哭鼻子,却在关键时刻敢于独自面对三百敌人的十六岁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