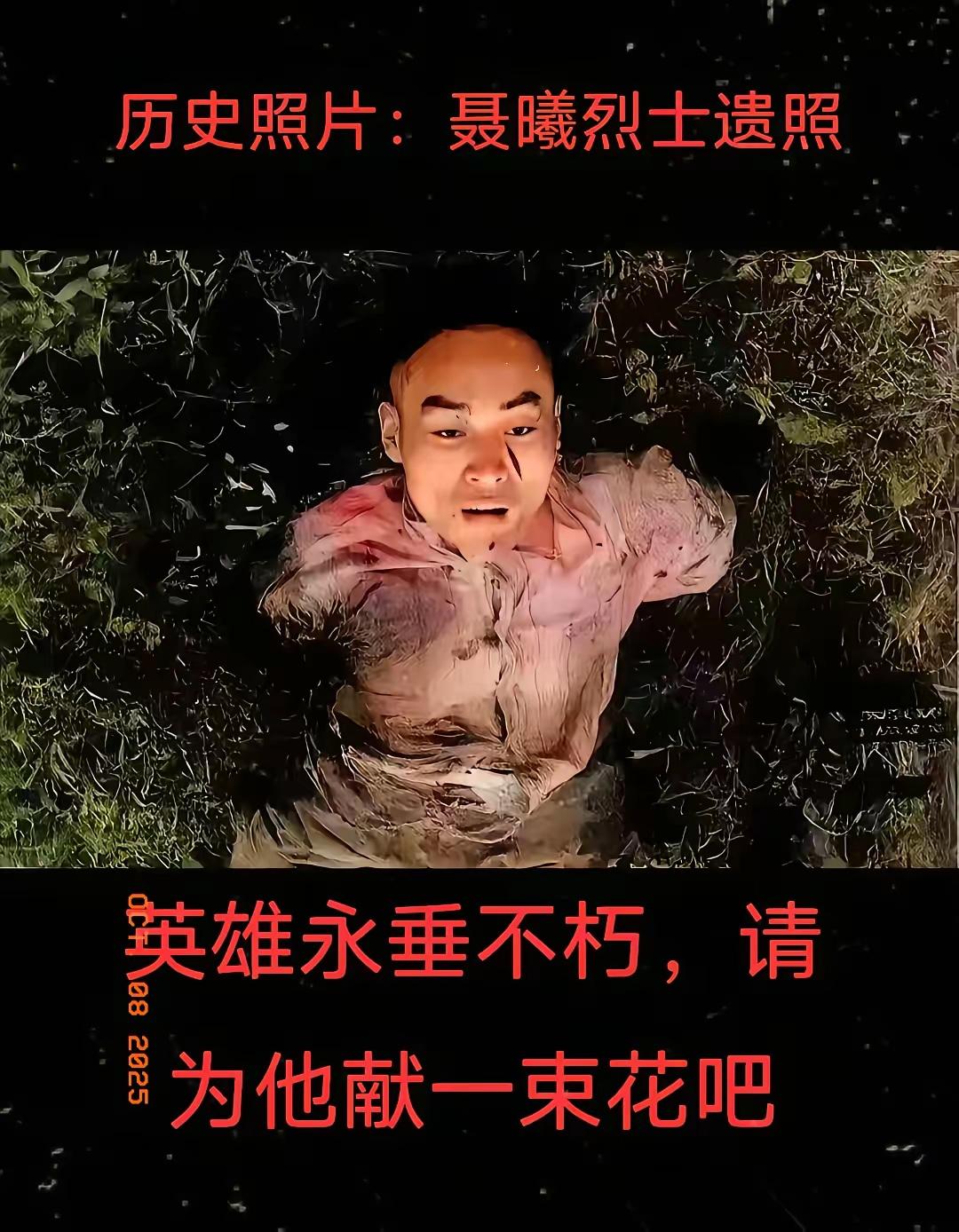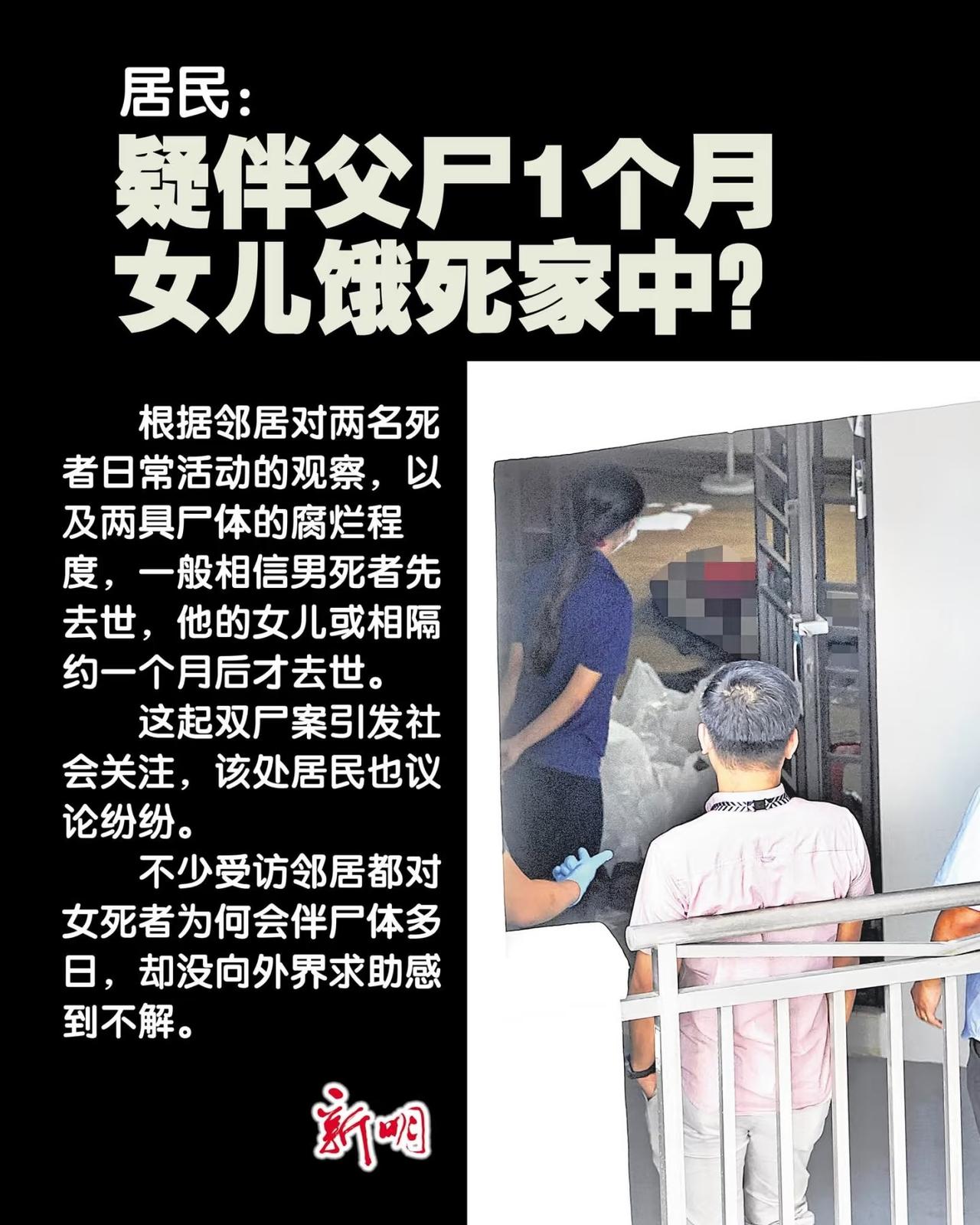一个女学生,深夜,把一个骨灰盒死死地绑在自己身上。然后,扔掉所有行李,纵身跳进冰冷的海里,偷渡上岸。她必须把这个湿漉漉的骨灰盒,亲手交到另一个人手上。盒子里装的,是陈宝仓将军。 在几个月前,他和他的老同学、老战友吴石将军,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 海水像无数根冰针,扎进她单薄的衣衫,顺着领口往骨头缝里钻。可她连瑟缩一下都不敢,只双手死死护着胸前的骨灰盒——那重量压在心上,比海里的暗流还沉,却也是唯一能让她撑下去的念想。 —— 她叫林巧玲,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三年级,表面上是乖乖女,实则是我党外围交通员。1949年冬天,她随学校南迁到香港,白天上课,夜里给《大公报》翻译外电,其实是替地下党传递情报。陈宝仓将军是她父亲的老上级,也是她从小喊“陈伯伯”的人。她最后一次见将军,是在九龙城寨的一家茶餐厅,将军把一叠微缩胶卷塞进她书包,摸摸她的头:“小姑娘,好好念书,也好好走路。”没想到,那竟是永别。 几个月后,将军与吴石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罪名是“通敌”。尸体由慈善堂草草火化,骨灰被随意埋在沙仑荒滩。组织决定:一定要把将军的骨灰偷运回内地。理由很简单——他生前不能回家,死后也要落叶归根。于是,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落在了林巧玲身上。她不会游泳,也没出过海,但她会说英语,能应付港英水警盘查;更重要的是,她信得过,也豁得出去。 跳海那天是1950年4月15日,凌晨两点。她先把自己脱得只剩内衣,然后把骨灰盒用帆布绳横竖捆了三道,紧紧绑在胸前,外面再套一件黑色雨衣。所有行李——学生证、口红、换洗衣服、甚至母亲的照片,全扔进岸边礁石缝,她连回头都不回,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陈伯伯”送回家。海水一浸,雨衣像纸一样贴在皮肤上,冷得她直打哆嗦,可她还是一头扎进浪里,像扎进一场没有退路的考试。 游的过程,她后来回忆,就像“把整个大学四年级重新上一遍”。浪头一个接一个,打得她眼冒金星,嘴里全是咸腥味,帆布绳勒得胸口发麻,她却不敢松手,生怕一松,骨灰盒就会被暗流卷走。中途,一艘港英巡逻艇的探照灯扫过来,她赶紧沉进水里,憋气憋到耳膜嗡嗡响,才悄悄探头换气。就这样浮浮沉沉,漂了将近三小时,终于摸到对岸大鹏湾的礁石。上岸那一刻,她两条腿软得像面条,手指被牡蛎壳划得血肉模糊,可她第一件事,还是解开绳子,把骨灰盒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上岸后,她没敢停留,连夜赶路,靠一双赤脚走了二十多里山路,脚底磨出好几个血泡。天亮时,她遇到一个赶集的农妇,用两块番薯换了一身干衣服,又把骨灰盒藏在竹篮里,上面盖满野菜。一路颠簸,她终于在第三天傍晚,抵达惠州境内的交通站。接待她的是一位姓李的老交通员,看见她浑身是伤,眼泪当场就下来了:“姑娘,你背的是火种啊,不能灭。”林巧玲却笑,一笑就扯裂嘴角:“李叔,我背的是咱家的长辈,得让他先回家。” 组织为将军举行了简单迎接:一张白布、一面党旗、一张遗像。她把骨灰盒轻轻放在桌上,退后两步,鞠了一躬,声音沙哑却坚定:“报告,任务完成。”然后整个人像被抽掉骨头,瘫在地上。医生后来诊断:重度脱水、肋软骨断裂、十指感染。她却只问一句:“将军,算光荣吗?”旁边老兵红着眼答:“算,算!” 将军的骨灰最终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与七十二烈士为伴。每年清明,林巧玲都会去墓前放一包陈皮梅——那是将军最爱的零嘴。她说:“糖我给带到了,您慢慢吃,别再操心。”再后来,她成了一名中学老师,教英文,也教历史,却从不把自己这段经历当“英雄事迹”讲,只在黑板角落写一句话:“海把我送过去,我把他们送回来。”学生们不明就里,她却笑:“你们长大就懂了。” 我读到她的日记,是在厦门一个旧书摊,本子被虫蛀得只剩半册,我却站在太阳底下,浑身起鸡皮疙瘩。回家路上,我买了包陈皮梅,咸甜带酸,一口下去,像咬破了1950年的海风。那一刻我明白,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章节,是某个姑娘用十九岁的骨头,背回一个将军的灵魂。我们今天的“回家”,是有人先跳了海;我们说的“团圆”,是有人先把自己撕成半块。想到这儿,我把剩下的陈皮梅撒进海里,小声说:姐,糖管够,您歇会儿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