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年贪污多少?”雍正对年羹尧说出这句话,可当年羹尧说出一年65000两时,雍正不仅没惩罚他,反而很欣慰,为何? 想弄明白雍正心里的小九九,咱们得把时间往前倒一倒,回到那场惊心动魄的“九子夺嫡”。 康熙爷晚年,儿子们为了皇位斗得你死我活,最后胜出的是平时最不起眼的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他这个皇位坐得可一点都不稳,外面有兄弟盯着,朝中有老臣看着,背后还有一堆烂摊子等着。 这时候,雍正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能帮他镇住场子、稳住江山的铁杆心腹。而年羹尧,就是他手里最锋利的那把刀。 年羹尧不光是雍正的大舅子,更是当时朝廷里数一数二的能臣。康熙三十九年就中了进士,一路从四川巡抚干到川陕总督,手里攥着西北几十万大军的兵权。雍正能顺利登基,离不开年羹尧在西北稳住大后方,震慑他那个手握兵权的十四弟胤禵。 所以,在雍正刚坐上龙椅那几年,他和年羹尧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不如说更像合伙人。一个在内主持大局,一个在外稳定边疆,配合得天衣无缝。雍正给年羹尧的信里,那叫一个亲热,什么“朕实不知如何疼你”之类的话,肉麻得都快不像个皇帝了。 在这种背景下,再来看那场关于贪污的对话,味道就全变了。 雍正问“你贪了多少”,他真正想听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态度。他想知道,你年羹尧在我面前,是不是还说实话?你心里有没有鬼?你拿的那些钱,敢不敢摆在台面上跟我说? 而年羹尧回答“六万五千两”,这个回答妙就妙在“诚实”。他没有哭穷,没有抵赖,而是大大方方承认了。这一承认,在雍正听来,就是一种姿态:皇上,我虽然拿了钱,但我对您没藏着掖着,我心里还是有您的。 在那个皇位还不算十拿九稳的时候,这种“忠诚”的姿态,远比六万五千两银子值钱得多。雍正要的是一把听话的、能办事的刀,至于这把刀平时需要用金子来养护,那都是可以商量的成本。所以他欣慰,是因为年羹堯通过了这场忠诚度测试。 当然,雍正的欣慰也不全是政治作秀。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他比谁都清楚,带兵打仗,治理一方,光靠朝廷那点死工资是远远不够的。 年羹尧镇守的西北,是什么地方?那可是清朝的边防前线,环境恶劣,民族关系复杂,叛乱时有发生。手下几万大军,吃喝拉撒、武器装备、人情往来,哪一样不需要钱? 所谓的“六万五千两”,在雍正看来,很可能就是年羹尧维持这支庞大军事集团运转的“润滑剂”。犒赏有功的将士,收买地方的头人,打点朝中的关系,这些事不上台面,却是维系一支军队战斗力和忠诚度的潜规则。 年羹尧如果真是个一清如水、两袖清风的圣人,他手下那些如狼似虎的将士,凭什么死心塌地跟着他在冰天雪地里卖命? 雍正心里有数,只要年羹尧能把西北的叛乱平定,把边疆守稳,这六万五千两就是一笔划得来的投资。他怕的不是年羹尧贪钱,而是怕他贪了钱还不办事,或者贪得没了边,忘了自己姓什么。 所以,当年羹尧说出这个数字时,雍正心里可能还嘀咕了一句:才六万五?比我想象中少多了。这说明年羹尧虽然贪,但还有分寸,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一个有能力、懂分寸、还忠心的大将,花点钱养着,值! 可惜,年羹尧没能一直保持这份“清醒”。 随着西北战事大捷,年羹尧的功劳也达到了顶峰。他被封为一等公,加太保衔,权势熏天,俨然成了“西北王”。这时候,他开始飘了。 他给自己手下的官员叫“年选”,公然培植私人势力;文武官员见他,得先行跪拜大礼;他给雍正上奏折,口气也越来越随意,甚至把自己和皇帝相提并论。 这些举动,彻底踩了雍正的红线。 当雍正的皇位已经稳固,内外再无强敌时,君臣之间的“合伙人”关系就结束了。雍正需要的,不再是能干的“刀”,而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奴才”。 而年羹尧这把刀,不仅锋利,还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甚至想反过来握住主人的手。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容忍的。 于是,那曾经被雍正“欣慰”地看在眼里的“六万五千两”,连同后来查出的侵吞军饷百万、收受贿赂四十余万的惊天巨贪,都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雍正三年,风向突变。曾经雪片般飞往年羹尧府上的赞美奏折,一夜之间变成了弹劾的罪状。朝廷议政大臣和刑部最终给他罗列了92款大罪,洋洋洒灑,从大逆罪到贪腐罪,应有尽有。 但仔细看就会发现,贪渎罪和侵蚀罪排在很后面,真正要他命的,是排在最前面的“大逆”“欺罔”“僭越”。说白了,年羹尧的死,不是因为他贪了多少钱,而是因为他不懂得收敛自己的权力欲,挑战了皇权的底线。 最终,雍正赐年羹尧自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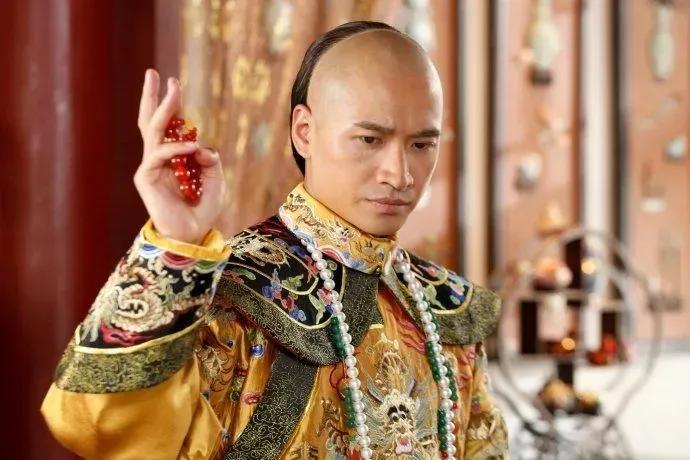


![乾隆真是职业皇帝名不虚传[吃瓜]](http://image.uczzd.cn/514115608926668554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