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战区地雷多如牛毛,一次国庆节会晚餐,我军一位团参谋拿着三个空酒瓶子,从堑壕里随便往外扔,三个酒瓶砸响了三颗地雷。 山里的风一阵阵吹下来,带着潮湿的味道。 麻栗坡的老乡常说,这风里裹着雷的气息。别笑,这可不是迷信。 老山一带,随手丢个石头,就可能炸起一片火光。 有人还记得八十年代,那位参谋酒喝高了,拿三只空瓶子往堑壕外一扔,跟着“嘭、嘭、嘭”,三朵土烟在夜里窜起,满桌人都傻了眼。 酒意散得比风还快。 那时候,地雷多得跟荒地里的石头一样,脚下哪怕轻轻一碰,都能要命。 战争停火了,可雷没停。山脊上的老树一圈圈年轮长出来,脚下却埋着上百万枚不同年代、不同制式的炸药。 越军埋的,我军也埋过。 要守住阵地,没办法,只能把地雷像麦子一样撒下去。 雨季来了,泥石流冲刷,埋得规整的雷群被搅乱,滚到沟里、卡到石缝里,甚至挂在树枝上。 日子久了,没人能说清这里到底藏着多少颗。有人说一百万,有人说两百万,数字在传,可没有人敢走进去数。 离老山不远的八里河村,村口竖着黑色的牌子,上面画着骷髅头。 村民看得麻木了,该上山还是要上山。 日子总要过下去。这个村子不过两百来人,几十年下来,死伤的名册长得吓人。有人割草,镰刀碰到坚硬的铁片,还没反应过来就炸开;有人插秧,脚下一踩,半条小腿不见了;有人去砍柴,火光一闪,父亲倒在儿子眼前。邹家的遭遇在村里流传得最广,父亲死了,弟弟死了,大哥和老三都成了残疾,只剩一个健全的老二。 人和地雷长期待在一块,会生出一种古怪的关系。害怕?是害怕的,但怕久了就钝了。有人甚至敢拿雷当玩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手里抱着铁疙瘩笑嘻嘻,下一秒全村人抬尸。也有人干脆自学扫雷,锄头、喷壶,硬生生刨出几十上百枚。那不是勇敢,是被逼的。地雷成了生存的一部分,就像地里的石头,得想办法搬走。 可真正要清干净,没那么简单。1992年,第一次大扫雷,部队背着炸药筒上山。那时候条件差,战士们一天就吃两顿,野外啃压缩饼干。两年下来,扫掉一部分,但村民还是不断触雷。1997年,规模更大的扫雷开始了,两年间五十多万颗地雷被清理,十八万件爆炸物被挖出来,触雷事故明显少了。每次清完一块地,部队会手拉手唱着军歌从雷场走过,像是在告诉老乡:你们可以放心了。 2008年,又来了一轮。这一次是配合勘界,把一些危险地段扫出来。可留到最后的才是真正要命的。2015年起,第四轮扫雷,面对的全是最复杂的山地。坡度七八十度,战士们要拴着绳子吊在崖壁上,一寸一寸地探。探针推进的间距只有三四厘米,手指要赤裸着感受泥土里细微的变化。汗水顺着袖口流进手心,谁都知道,一个抖动,可能就炸掉半条命。 牺牲也在所难免。程俊辉,九零后,原本是连里最舍不得放走的人,他偏要去扫雷。在一次陡坡作业中,发现一枚引信,话音还在耳边,脚下的巨石松动,他整个人坠下山坡,没能再起来。那句“我发现一枚引信”,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杜富国更是被人反复提起,他喊着“你退后,让我来”,结果双手没了,双眼失明。血肉之躯硬生生替老乡们挡下危险。 这场排雷,不只是军人的事。八里河的村民盼了几十年,有人激动得掉泪,有人杀羊送到营地,还有人抱着孙女认战士做干爹。那是发自心底的感激。因为他们太清楚了,没有这些人,生活永远走不出阴影。扫雷不仅是挖地里的炸药,更是给人重新一块可以种田、可以走路的土地。 到2018年,边境两千多公里,六百五十个雷区,已经清掉六百个。剩下的五十个,因地形过于险恶,被封围起来。有人说,等它们自己坏掉不就行了?不行。塑胶壳的雷能存活一百多年,雨水和泥石流让它们位置更飘忽。危险从未减少,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 二十六年,四轮扫雷,跨越两代军人。有人负伤致残,有人献出生命。每一次扫完,唱着歌手拉手走过雷场的身影,是最有力的画面。那不是表演,而是一种保证。村民抬头看,眼睛里带着泪。 山林依旧在,风依旧吹,虫鸣还是那么聒噪。不同的是,更多地方能听到锄头刨地的声音,孩子们的笑声,炊烟一点点升起。夜色里,远远还能看到黑色警示牌立在封围区口,骷髅头在风中摇晃。地雷还没彻底消失,可人们的脚步,已经慢慢走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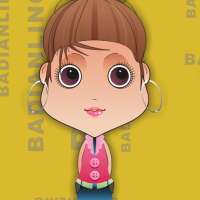
乌龙院
致敬我们的英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