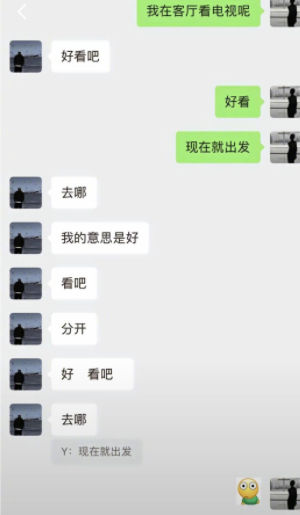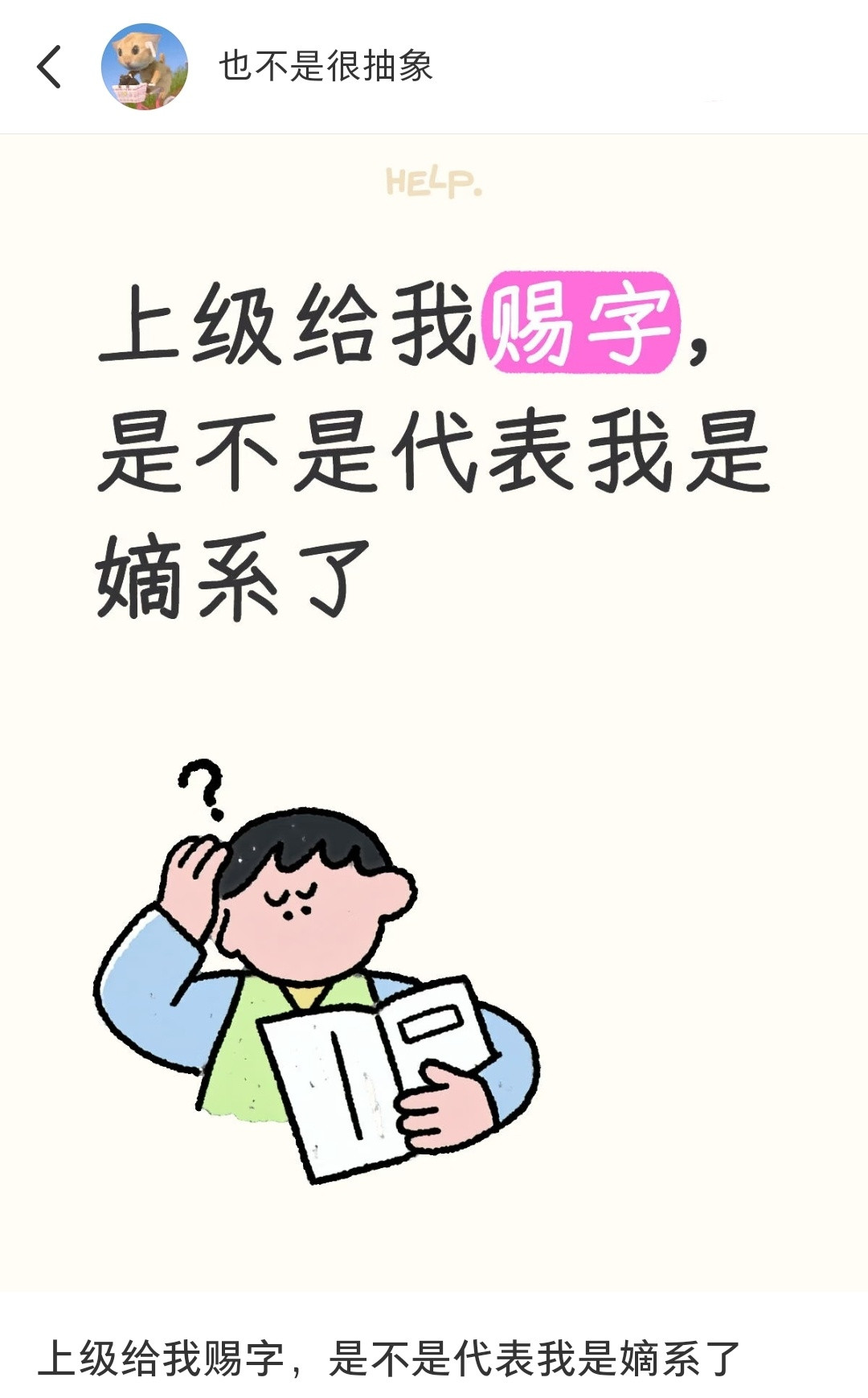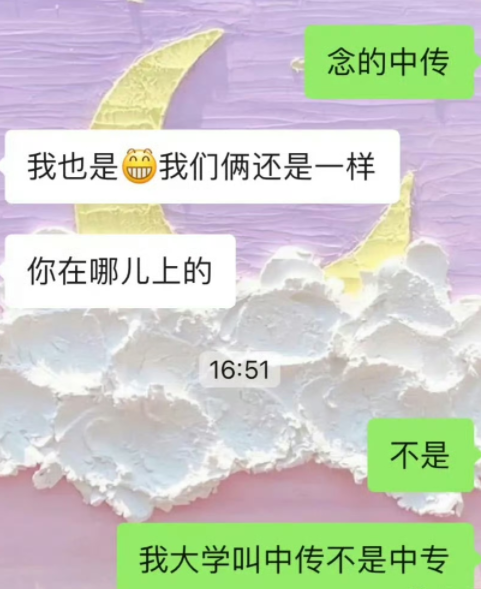26年前,余秋雨夜访一位画家,画家拿出一份仇人名单:“每死一个,我就用红笔划掉一个名字!”回到家后,余秋雨也写下四个仇人名单:浅芳丽莎! 1999 年的一个雨夜,余秋雨拜访的画家,是他早年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时结识的挚友 —— 姓陈,人称 “陈疯子”,画的山水曾被业内赞为 “带血的墨色”,可十年前一场变故后,便淡出了公众视野,隐居在老城区的弄堂深处。 陈画家探出头来,看到余秋雨,他先是愣了两秒,随即眼睛一亮,伸手一把拉住余秋雨的胳膊,力道大得让余秋雨愣了愣:“秋雨!你怎么找过来了?这雨下得邪乎,快进来,别冻着!” “坐,坐!” 陈画家拉着余秋雨在八仙桌旁坐下,转身从柜里拿出一个粗瓷茶杯,用热水烫了烫,又从一个铁皮罐里抓了把龙井,撒进杯里,冲上热水。 “你可是稀客,上次见还是三年前,在美术馆的画展上。” 陈画家搓了搓手,指尖沾着的颜料蹭在袖口上,留下一点淡青色的印子,“最近在忙啥?我看报纸上说,你又出新书了?” 余秋雨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还能忙啥,走了些地方,写了点东西。”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只是…… 烦心事也多。” “陈兄,你不知道,《文化苦旅》出版后,我是真没想到……” 他抬起头,眼底带着几分疲惫,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委屈,“有人说我写的是‘文化快餐’,没深度;还有人说我借历史炒作自己,甚至…… 甚至编了些谣言,说我家人的坏话。”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微微发颤:“前阵子,有个评论家用了整整三篇文章骂我,说我‘背叛了学术’,还翻我几十年前的旧事,鸡蛋里挑骨头。我女儿在学校,同学拿着报纸问她‘你爸爸是不是真的像上面写的那样’,孩子回家哭着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余秋雨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指着上面的文章,字里行间满是尖锐的指责,有些地方还被人用红笔圈了出来,笔画用力得几乎戳破纸页。 陈画家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我懂,我太懂这种滋味了。” 他站起身,走到画案旁,拉开下面的抽屉 —— 抽屉里塞满了画纸、颜料,还有几个用红绳系着的小布包。他在里面翻了半天,终于拿出一个深蓝色的布面本子。 “你看看这个。”余秋雨疑惑地拿起本子,偶尔有几页画着简单的素描,翻到最后一页,他停下了 —— 那一页用黑色的钢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字体遒劲,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行小字,像是备注。 有些名字被红色的钢笔狠狠地划掉,红线又粗又深,几乎把名字完全覆盖,边缘还留着墨水晕开的痕迹,看得出来,划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 “这是……” 余秋雨抬头看向陈画家,眼神里满是疑惑。 “我的仇人名单。” 陈画家说:“你看第一个名字,李建国,当年就是他伪造证据,毁了我的画展。” 他指着那个没被划掉的名字,手指微微收紧,“还有这个,王志强,我当年带的学生,偷走了我两幅没完成的画,改了签名,拿去参赛拿了奖,还到处说我教的东西没用。” 他的声音很平静,可余秋雨能听出里面藏着的委屈和愤怒,像是积压了多年的洪水,只是被他强行拦在堤坝里。 “那这些被划掉的……” 余秋雨指着那些盖着红线的名字,小声问道。 陈画家放下茶杯,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有释然,也有几分无奈:“这些人,都没了。” 他顿了顿,目光飘向窗外的雨幕,像是在回忆什么,“前年冬天,李建国在医院病逝时,我没去参加他的葬礼,只是回家后,找出这个本子,用红笔把他的名字划掉。划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不是恨,是觉得…… 没意思。” “没意思?” 余秋雨皱了皱眉。 “是啊,没意思。” 他看着余秋雨,眼神很认真,“秋雨,我不是教你记仇,只是有些伤害,不是说忘就能忘的。但报复没用,你越恨,就越会被仇恨绑着,走不出那个圈子。我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不是为了等他们死,是为了提醒自己,我受过的苦,不能白受。” 晚上,余秋雨回到家里,他在书房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四个字:浅芳丽莎。 这四个字代表着四个人 —— 古远清、余杰、萧夏林、沙叶新。 古远清曾在多个场合公开批评他的作品,说他的《文化苦旅》“缺乏学术严谨性”,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质疑他的学术背景; 余杰则写了一本专门批评他的书,里面充满了尖锐的指责,甚至编造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谣言,让他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萧夏林更是在网络上发起了对他的 “声讨”,号召网友一起抵制他的作品,还曝光了他的私人信息,让他和家人受到了很多骚扰; 沙叶新则在一次文化论坛上,公开称他是 “文化商人”,说他的作品 “充满了铜臭味”,让他在文化圈里颜面尽失。 余秋雨看着那四个字,没有愤怒,只有平静。他想起陈画家说的话,“把名字写下来,是为了提醒自己,受过的苦不能白受”。 他写下这四个字,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等他们 “被划掉”,而是为了告诉自己,这些伤害他都记得,但他不会被这些伤害打倒。他要带着这些记忆,继续走自己的路,写自己的字,就像陈画家,即使被毁掉了画展,也没有放弃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