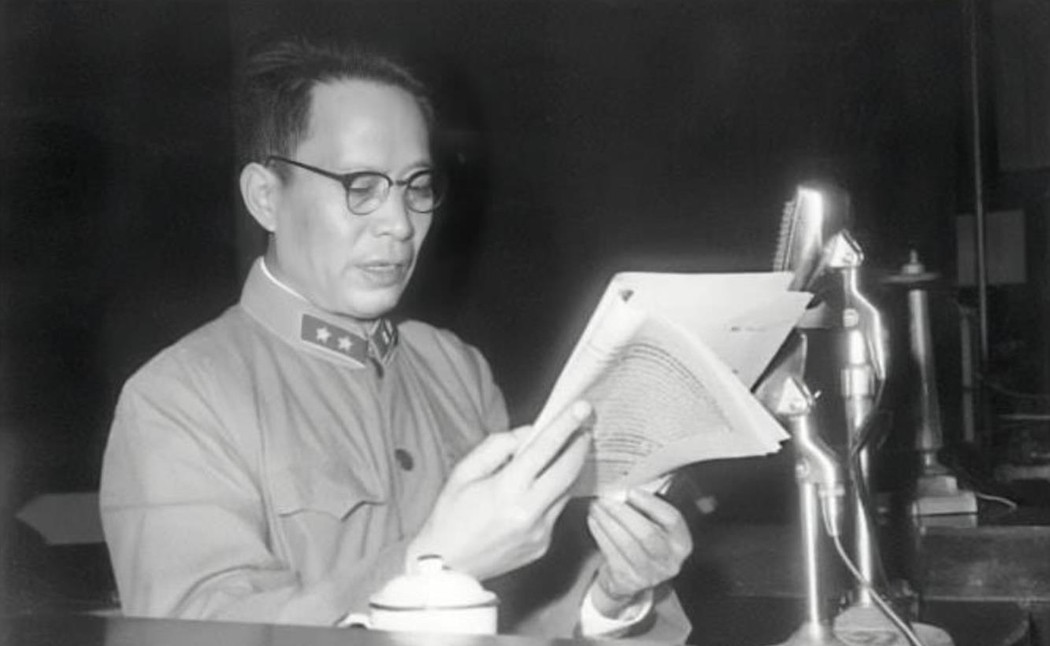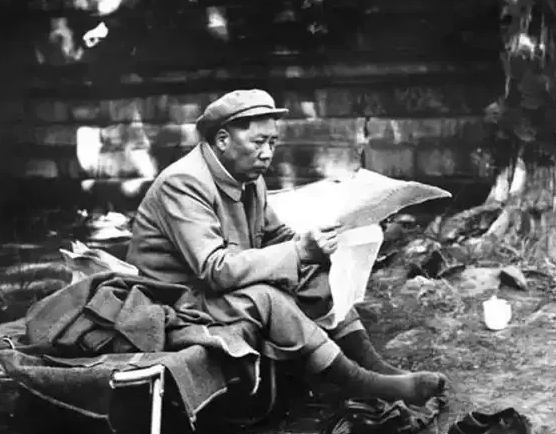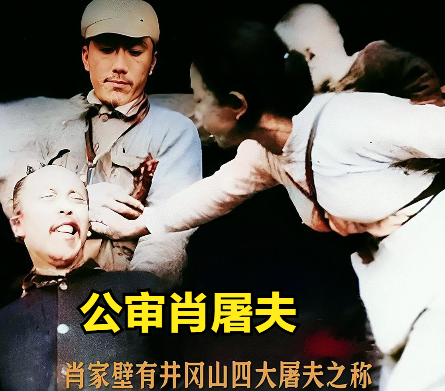1971年,重病的浙江副省长冯白驹写了一封求救信,伟人读后,立即派人喊来广州军区丁司令,问:"你认不认识冯白驹?"丁司令答:"知道,只是不熟悉。"伟人讲:"派专机接他,去你们广州军区好不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1年的夏天,浙江医院的一间病房里闷得透不过气,窗外的梧桐叶在热风里微微晃动,病房里却安静得只听见沉重的呼吸声,病床上的冯白驹,面色蜡黄,双手颤抖,握着一支钢笔在纸上缓慢移动。 纸张不是正规的信笺,而是皱巴巴的纸片,甚至还带着消毒液的痕迹,几个字写得东倒西歪,却包含着他最后的力气,那是一封求助信,也是他唯一的希望。 这封信几经辗转送到北京,读信的人眉头紧蹙,短短几行字写出了病情的严重,也透露出他心底的愿望。 他没有提及功绩,只是请求能活下去,还想再回海南看看战友的坟,也想再看一眼自己亲手开出的橡胶林,指示随即传下去,行动必须立刻展开,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救援,就这样开始了。 广州军区接到命令后,反应迅速,专机立即准备,医疗小组在最短时间集结,连紧缺的进口药品都被紧急调拨,那一夜,杭州的机场灯火通明,担架上的冯白驹呼吸微弱,血压已经低到危险边缘。 身上的军毯盖住瘦削的身躯,左手还紧紧握着一个褪色的旧枪套,那是他当年率部坚持游击时的遗物,真正的手枪早在文革时期被抄走,只剩下这个皮套陪着他。 当飞机滑行起飞,机舱内的灯光忽明忽暗,心电监护仪滴滴作响,医护人员紧张地守在床边,不时调整氧气管和点滴,窗外是漆黑的夜空,机身划过厚厚的云层,朝着南方飞去。 抵达广州时,东方刚刚泛白,救护车早已等候在跑道边,军区负责人亲自到场,神情凝重地望着这位几乎失去意识的老人,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这场救援并不仅仅是为了挽救一个病人。 冯白驹并非普通干部,他的一生与海南的山林紧密相连,1927年,国民党清党血洗海南时,他才二十多岁,身边只剩下二十几名战士,带着他们钻进五指山,靠野果和泉水维持生存。 最危险的时候,队伍濒临瓦解,他却咬牙撑下去,他告诉身边的人,山可以不藏人,人要互相藏护,正是这种信念,让队伍在丛林里坚持了下来,后来,这支小队伍逐渐壮大,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琼崖纵队。 抗战期间,他们在南渡江打响了海南抗日的第一枪,武器简陋,装备落后,却始终没有退缩,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有数千人跟随他转战山林。 外国人甚至称他是孤岛上的“国际英雄”,1950年解放海南岛时,他的部队里应外合,帮助主力击溃十万守军,对共和国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一战。 建国后,他转任地方工作,先后担任海南区党委书记、浙江副省长,1950年代末期,因为各种原因,他的职务被撤销,还被扣上“地方主义”的帽子。 曾经叱咤风云的“琼崖铁汉”,一度被安排到基层做副县长,甚至在养猪场里管理过牲畜,可是他没有抱怨,而是把心思转向橡胶种植。 那个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橡胶禁运,国防和工业建设迫切需要替代来源,冯白驹带着退伍军人和知青扎进海南的原始雨林,光脚踩在泥水里,带头示范如何割胶。 蚂蟥爬上腿,吸得鲜血直流,他也只是随手一抹继续干,凭着这种拼劲,到1958年,海南橡胶产量已经占全国大部分需求,被称作“白色黄金”,这些橡胶制成的轮胎、军工产品,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基础。 在病榻上,他依旧惦记的还是橡胶事业,他希望能把橡胶推广到五指山的更高地带,即使当时技术条件还难以实现,他的生命已经被一点点消耗殆尽,可心里装着的仍是那片山林和那片树海。 在广州军区医院的日子里,他经过数月的治疗病情才稍有缓解,即便吊着点滴,他仍坚持去看试验田,叮嘱技术员怎样移栽。 他甚至推开搀扶的警卫,嘴里还说,当年打游击摔断腿也一样能翻山,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海南橡胶的未来上。 1973年夏天,冯白驹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岁,追悼会上,老战友神情悲恸,人们忽然想起,琼崖纵队坚持二十三年没有领过中央一分钱军饷,全靠百姓支援和自己坚持走下去。 这段往事让人感到既沉重又敬佩,海南百姓至今仍记得他,当地黎族群众把连绵成片的橡胶林称作“冯公送来的绿色银行”。 每到清明时节,总有人自发来到他的墓前,带上一罐橡胶乳液浇在墓碑前,作为最质朴的纪念。 那封求救信现在依然保存着,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渐渐模糊,可它见证了一个老人临终前的坚韧与牵挂,它不仅仅是一封信,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一位革命者的生命,在关键时刻被国家重新接住,也让后人再次记起他曾经创造的奇迹,对海南人来说,那片橡胶林就是最好的纪念碑,告诉世人,有人曾用全部的热血和信念,把荒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冯白驹: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