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2年叛逃去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有维族和哈萨克族为主,大约有五六万人,现在他们过的一点都不好。 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的旧货市场里,有个摊位总摆着本泛黄的证件册。 摊主是个叫巴图尔的中年男人,证件册里夹着的苏侨证编号早已模糊,照片上的维吾尔族青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袷袢,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这是他外公 1962 年离开新疆时办的证件,如今成了他研究家族史的唯一实物。 外公常说,当年要不是那两个穿军装的人,他绝不会离开伊犁河谷的果园。 1962 年初春,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少将带着翻译来到村里,在打麦场上铺开苏联地图,用红笔圈出大片土地,说只要填了表,每家都能分到比老家大三倍的耕地。 同来的祖农・太也夫少将更实在,带来的卡车里装着面粉和棉布,挨家挨户发放。 他说自己刚从苏联考察回来,那边的集体农庄顿顿有肉吃,孩子上学不花钱。 巴图尔的外公摸着家里空荡荡的面缸,想起刚熬过的饥荒年,心一横就填了申请。 那年春天,像外公这样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边民,一共有六万多人离开新疆。 塔城地区的牧民最集中,光阿西尔乡就走了两千多户,连乡小学的维吾尔语老师都跟着走了,黑板上还留着没写完的算术题。 苏联领事馆的季托夫副领事也没闲着,开着伏尔加轿车在边境村镇转悠,车里的广播喇叭反复播放着俄语歌曲,逢人就发印着西伯利亚农场的挂历。 有老人记得,挂历上的拖拉机崭新发亮,田埂上堆着小山似的麦垛。 可到了苏联境内,景象完全变了样。外公和其他青壮年被编入伐木队,乘火车往西伯利亚走了七天七夜。 到达营地时正赶上寒流,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八度,带去的羊皮袄根本抵不住风雪。同队的三个同乡,冬天还没过完就冻饿去世了。 更让人心寒的是那两位少将的境遇。 外公在集体农庄见过祖农一次,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正给苏联官员讲解新疆的毡房搭建工艺,身后跟着两个面无表情的卫兵。 后来才听说,马尔果夫被安排在农庄当统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登记牛羊数量。 1965 年夏天,外公偷偷给老家捎过一封信,托过境的商人带回去。 信里说西伯利亚的蚊子比马蜂还大,面包要凭票供应,当初承诺的耕地根本没影子。 可这封信石沉大海,再也没收到回音。 苏联解体那天,巴图尔的母亲正在织地毯。 收音机里突然响起哀乐,播音员用颤抖的声音宣布国家解体,母亲手里的毛线团滚到地上,半天说不出话。 从那天起,他们的粮本作废了,医疗卡成了废纸,孩子上学要给学校交哈萨克语补习费。 1993 年,巴图尔跟着外公去了趟霍尔果斯口岸。 八十岁的老人拄着拐杖,在铁丝网前哭了整整一天,手里举着那张苏侨证,用生硬的汉语喊:“我是中国人,让我回家。” 可边防站的军官指着墙上的公告说,1962 年的离境者已自动丧失国籍。 现在巴图尔在市场上修鞋,常有人拿着苏联时期的旧物来问价。 有次收到个维吾尔族老汉的铜手鼓,鼓面上刻着 “伊宁” 字样,老人说这是父亲当年从新疆带过来的,现在孙子连维吾尔语都不会说了。 历史学者说,这种被外部势力诱骗导致的族群离散,在中亚地区并不少见。 19 世纪末沙俄也曾用土地诱惑中亚牧民迁徙,最终这些人大多成了边疆开发的廉价劳动力,后代至今散落各地。 巴图尔最近在整理外公的日记,其中一页写着:“1962 年 4 月 22 日,过界时看到霍尔果斯河的水是清的,以为能洗掉穷根,没想到只是换了个地方受苦。”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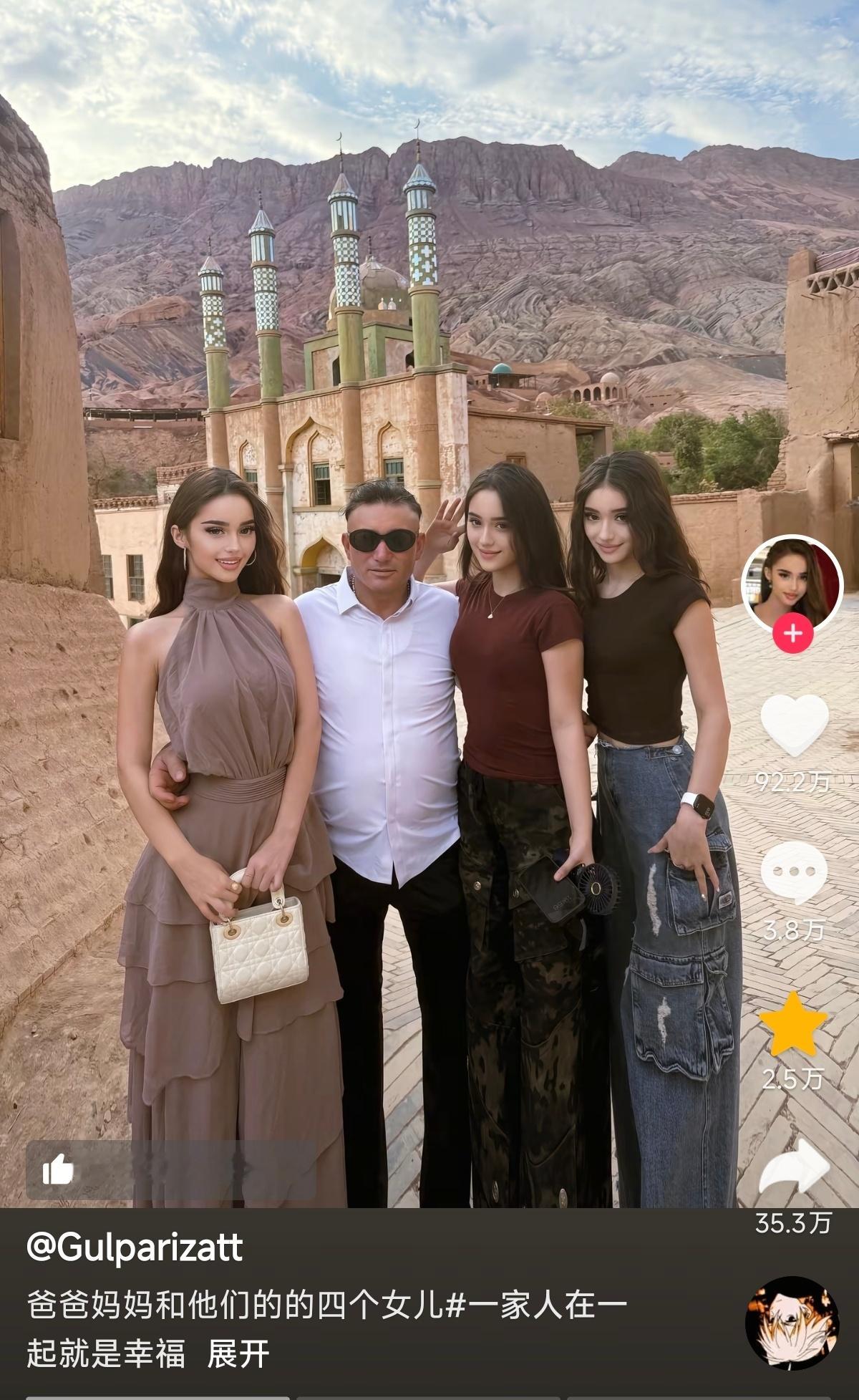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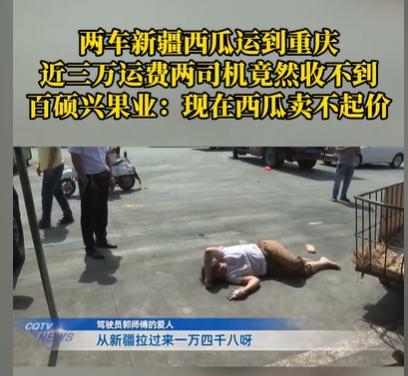




陶澎
小编你要是回到那个年代,你肯定跑台湾和香港
天园地方
最后都走
老胡
没必要黑化,在苏联解体前他们过的比新疆好,后面就是王小二了。
6689
历史如明镜[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用户15xxx00
活该
用户91xxx43
走了才好,否则内地的人怎么去那